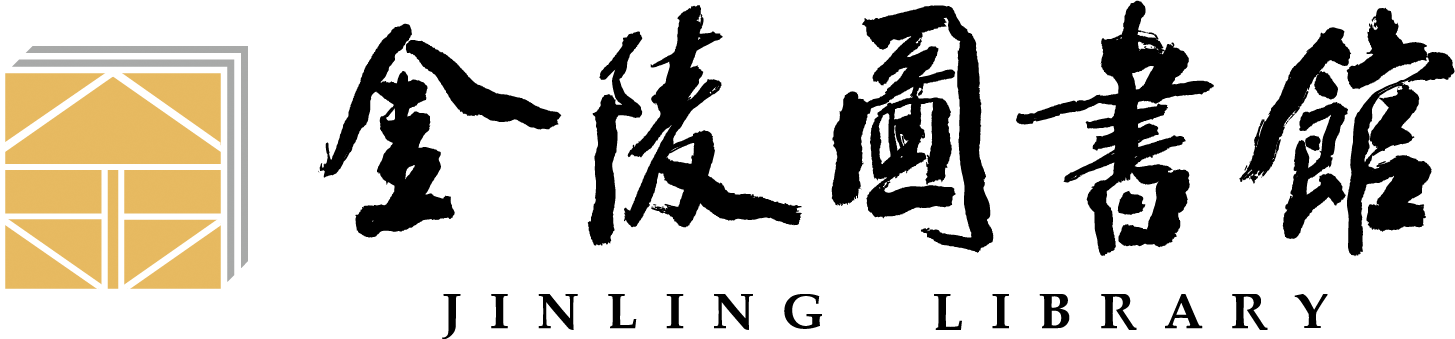![期刊架位号[5055] 期刊架位号[5055]](./W020251123326025712794.png)
“吃货”这个词本不是好话,然而互联网时代,大家习惯于以此自嘲,一时遍地都是吃货,便没贬义了。然而爱吃的人之间,也还是不同的。 我一位同学的爸爸,是四川内江人。一天,他开着车,我同学坐副驾驶位,还带了两位朋友。这位爸爸用手指敲着方向盘,忽然想起什么,吩咐我同学:“我开车腾不出手,你给家里打个电话,说,那个汤可以开始热了。我们还有15分钟到家,这样客人们正好来得及吃,味道刚好。”
还是这位先生。他女儿带准女婿初次见他时,迟了5分钟还是10分钟吧,全桌都等着。准岳父脸色便不大好,说:“来了,就坐下吃吧。”吃到后来,面色和缓了。他跟准女婿说:“别介意。有点不高兴,但不是针对你。就是这个鱼啊,端上来,凉了,就不大好吃了。”有一年他在海南,弄到一块极好的鱼肉。朋友都说,趁新鲜烤了吃好。他说不,打电话问朋友:“你们知道谁明天要过来?”找到一位当天下午到的朋友,又打去电话,让人带哪几种调料过来。挂了电话,他严肃地表示:“好鱼,不能随便吃!”
某年夏天,我带长辈们在法国南部到处晃荡,日常吃海鲜。夏转秋时,我去杭州做活动,当地一位老师很热情,活动结束后坚持要请我到杭州的某个大馆子吃潮州海鲜。我推辞再三,总被告知“别客气,别客气”。我心想,真不是客气啊!吃了半个夏天的海鲜了,您请我吃碗片儿川多好啊!隔天到苏州,一位在电台工作的朋友,一句不问,直接拉我去了个桌椅油黄的小店,坐下来点了鳝糊、糯米糖藕、黄酒、虾仁面,临了一大盆热乎乎的鲃肺汤。——身为江苏无锡人,至此感动到热泪盈眶:真是物质和精神上都遇到了知己。
我外婆说,我舅舅小时候性子很“揪”——这是土话“执拗”的意思。舅舅每次跟我外公吵完架,就把眼镜布塞眼镜盒里,拿几本书塞进书包,气哼哼地出门,在门口还会吼一声:“我再也不回来了!”外婆说,每到这时,她就叹一口气,走进厨房,打两个鸡蛋,坠在碗里的面粉上,加水,拌,加点盐,加点糖。直到面、鸡蛋、盐、糖勾兑好了感情,像鸡蛋那样能流、能坠、能在碗里滑了,就撒一把葱。倒油在锅里,转一圈,起火。看着葱都沉没到面里头了,把面糊碗绕着圈倒进锅里,铺满锅底。一会儿,有一面煎得微黄、有吱吱声、有面香了,她就把饼翻过来。待两面都煎得金黄略黑、泛甜焦香时,她把饼起锅,再撒一点儿白糖。糖落在热饼上,会变成有甜味的云。这时候,我舅舅准靠着门边儿站着,右手食指挠着嘴角。我外婆说:“吃吧。”我舅舅就溜进来,捧着一碗面饼,拿双筷子,吃去了。我外婆每次给我摊饼时都要讲这个故事,讲完了,饼给我,还要叮嘱:“烙黄的部分,蘸白糖;烙焦黑的部分,别蘸白糖。”她说,烙黄的部分蘸白糖,糯甜;焦黑的部分自带脆香,不蘸白糖好吃。后来我每次看法国朋友琢磨牡蛎配夏布利、甜点配波特酒之类时,都想到我外婆给面饼配糖的细致。
我外婆炖红烧鳝鱼,总是将头和尾都放在里面一起炖,到出锅时再将头和尾拿走。偶尔忘记,就会看见鳝鱼头还放在盘子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很吓人。我小时候老抱怨,觉得我外婆是吝啬,连鳝鱼头尾都不放过。很多年后,我自己下厨,也懂得了:虾,最鲜的部分在虾头虾脑;鱼头炖汤也鲜。我外婆保留鳝头,是想炖出点鲜味来。 从里斯本罗西奥广场往北走,到大斜坡那里,有几家凭斜坡建的老馆子。有一个店,是一对老夫妻开的。太太掌厨,老先生招呼客人。老先生胖胖的,很有福相。我们去时还早,没到饭点呢,店里还空着。坐下来笑问店家有什么拿手菜时,老先生说:“我太太做的,什么都好吃!不信,看我的体型!”我就乐了,要了份鲑鱼,要了份脆鳕鱼条,还要了波特酒。老先生帮太太打下手,很勤谨。手艺确实好。老先生看我们吃得香,咽了口口水,在我们对面的桌子前坐下,指着鳕鱼条对他太太嚷:“鳕鱼条,我也要一份!”太太就一边起灶一边笑,就像看见小孩闹脾气似的。我当时笑得快摔倒了,赶紧划拉一堆鳕鱼条给他老人家。于是大家一边吃一边夸:“好!”
在重庆吃火锅,我总以为,只有烫毛肚、鹅肠才要讲究火候。后来发现,有几位姐妹,烫酥肉、土豆和麻花,都编着号。我就开玩笑问:“是不是麻花也要分三成熟、七成熟的?”她们就认真纠正我:“九宫格中间一格温度最高,翻腾不止,不宜久煮,却适合涮烫,所以毛肚、黄喉,涮了即起。上下左右的四格温度次之,可以把肉片、鱼片搁那里慢炖。四角的格子温度最低,就适合把麻花、肥肠之类放进去焖煮。”她们一边说着,一边守着自己那边的酥肉、土豆、麻花、藤藤菜,默默算着火候。到差不多了,夹起来:“好吃!”
我曾经以为,松茸就该用来蒸蛋或者烤着吃。跟长辈们经过康定城区时,河旁的老菜场,有肌肤黝黑的老摊贩,皱纹里都镶着神秘感。你去问他们要松茸,一摇头,“被订掉了”。得看到你身边站着他熟识的某位,他才展颜,揭开地上篮子上的白布,给我们看松茸。我们带着松茸上了高原,住处颇为偏僻,我一路寻思,没好的厨具,怎么料理这松茸?到饭点,长辈就支起带上高原的一块铁板,掏出一堆切片五花肉,洗干净松茸;铁板加热,先下五花肉,熬五花肉的油;到五花肉油吱吱响、渐次变透明时,松茸切片,放在油上,须臾烤香,斟酌着手指撒薄盐,夹起来,一嚼,汁浓味鲜。长辈说,好松茸,不用多调味就好吃,但真不调味也不行。现熬出来的五花肉油,加一点盐,才不遮松茸的味道。他不辞辛苦,专门带了铁板、盐和好五花肉上来,就为了这一口。
前几天,在重庆较场口一家店面极小、树荫里摆桌的店吃牛肉面,看到有牛蹄花汤,就很好奇。店家劝我别一个人吃,吃不完,下次人多时再来吃,“吃了牛蹄花,就不想吃猪蹄花了”。我心想,还带劝退的。隔几天,俩人去,叫了牛蹄花汤,另要了番茄杂酱面,加牛小骨浇头,还想加五香牛肉,店主劝说不要——“番茄杂酱和五香牛肉味道不合!你要吃下次来再说!”我又想,还带劝退的。我们把牛蹄花连皮带筋带脆骨嗦完,吃了面,期间隔壁俩人一直在吹着电风扇边吃边聊,一位主说,一位捧哏。主说那位自己就是在秀山开牛肉面店的,也赶来吃一口。他说这个啊,应该是一锅加30克辣椒炒料后焖出来的,他自己开店,大概猜得出;说做牛骨和做牛肉不同,牛肉不怕过夜,牛骨、牛蹄这些熬汤,熬久了才“耙”才浓,但下了作料,过个夜味道就不好了……听着爱吃之人的讲解吃东西,会觉得东西都比平时好吃点。这也是重庆的一点好处:大家都爱讨论吃,听着,比一边吃饭一边听邻桌讨论创业融资员工培训对齐打法之类,要好得多。
想到世上还有这些爱吃的人,我便高兴起来:觉得这烟火人间,总还有乐趣。
(《读者(原创版)》2025年10期[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