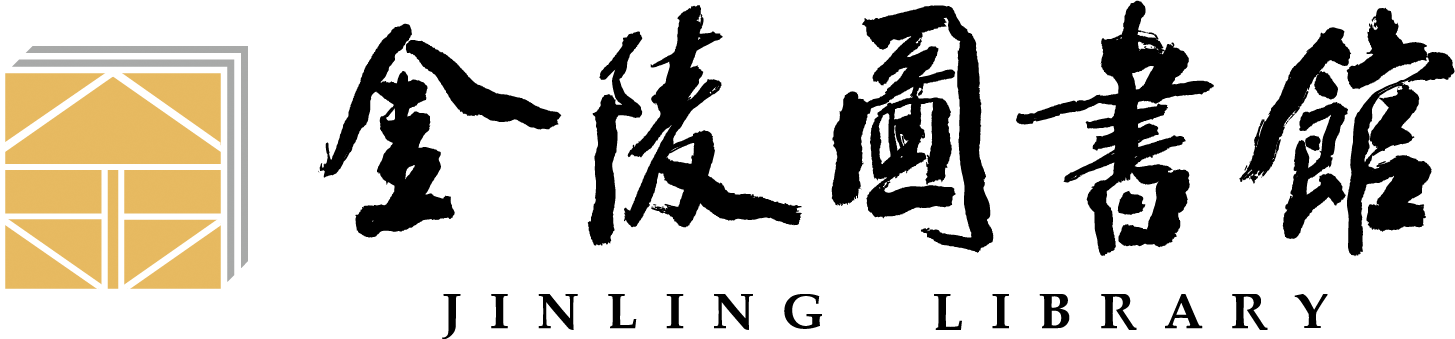![期刊架位号[5055] 期刊架位号[5055]](./W020251112600089680261.png)
文 | 明前茶
一
“客人,你的鸡蛋,跟前头5个人的一起打,可以吗?”
“当然可以。”
转眼间,小老板已经把6颗蛋敲入一个大海碗。他先用竹筷干净利落地搅打了十几下,随后将蛋液平分在6个蓝边碗中;接着,他的大勺子在不锈钢汤桶中搅动起来,汤羹旋转,汤桶里随即开了一朵花;随即,他手中的汤勺飞速滑入这朵花中,一勺饣它汤(徐州土话,音“啥汤”)便从高处冲入那预备好新鲜蛋液的碗中。蛋花翻腾,与汤迅速地融为一体。
前面5碗迅速被人端走,冲到第6碗时,我不禁夸赞一声:“你这冲汤本事,比四川人冲盖碗茶还要帅呢!”小老板听到我的声音,抬头打量我,忽然扔了勺子,喊道:“老师,你怎么来徐州了?我是小黄!”
他摘下口罩,真的是小黄,我数年前走访过的学生。他怎么干上这买卖了?见我一脸困惑,小黄把我引到离灶头最近的空位上,笑着说:“几年没见您了,生意又停不下来,委屈老师坐近点儿,我跟您唠唠。”
略有点跛足的他,用托盘端来饣它汤,又拿来徐州有名的“八股油条”。
喝一口饣它汤,那鲜美醇厚的口感让我赞叹——酒店前台的姑娘说这家店“有功夫”。小黄说,做这买卖,凌晨3点半就要开门,此时,送老母鸡和猪大骨的人已经到了。鸡和猪骨焯水后放入这个一米深的大锅,加葱姜,加满水,熬一个半小时,捞出大骨头,鸡要去皮、去骨,撕成鸡丝。鸡丝再加原汤熬煮,里头再加上麦仁、花生碎以及一个祛湿理气的中药料包,熬稠糊了,再撒上枸杞和少许豆腐干丝,最后用这滚烫的汤来冲鸡蛋。如此,用鲜、香、烫的一碗饣它汤开启一天,是徐州人的美好生活。
二
大学毕业后,因为身体原因,小黄找工作很不顺利,在隔壁县找到一份乡镇编外文员的工作,月薪3000块,干了近两年。“等我把乡图书馆里的书全看完了,那种孤单就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我外婆快80岁了,我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她不放心。我就回徐州了。我舅舅做饣它汤很有一套,我就跟他学了技术,自己开了这个小门面。”
做这种滚烫的小吃,一不小心就会被烫到。小黄给我看他双臂上被烫出的一溜儿伤疤,他眼睛里全是闪闪烁烁的往事。“做饣它汤的第一年,我差点坚持不下来。做小吃没法坐着,必须一直站立,我的两条腿又不一般齐,左腿使不上力,总是站到右边的胯骨发麻为止。”
我不由得叹息一声,为这孩子的坎坷命运。若我没记错,他今年28岁了,我上一回见到他还是10年前。那一年,他刚参加完高考,拿到一所二本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后,他的班主任就帮他报名了我们报社的资助大学新生上大学的项目。这位30年教龄的教师在电话中有点哽咽,她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8岁出车祸,失去了妈妈,自己的左腿也打了钢钉,从此左腿比右腿就短了两三厘米。“孩子虽只考了个二本,可这也是他过上像样日子的一个机会,希望你们能帮帮他。”
每年报社的这个项目都面临僧多粥少的问题。因此,在8月底向被资助者发放助学金之前,我们会派出很多个工作小组,去实地查看孩子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
于是,我们无意中打听到了小黄自母亲车祸去世以后的生活。
在妻子去世后,小黄爸爸为了排遣心中的哀伤,去外地帮人收麦子。干这种苦力活的人叫作“麦客”。就在收麦时,他爸认识了麦地主人家的女儿,那女子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做饭、送饭中,两人眉目之间有了那么一层意思。后来,这女子成了小黄的继母,又过了一年多,生了个儿子。
我们见到小黄爸爸时,他闷头抽烟,半天才说:“你们的资助计划,也只能管孩子一年。我这大儿子念了大学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现在就出去学门手艺。理发,做裁缝,做木工,都比上大学强啊。”
小黄想上学,外婆也想让他上学。最终谈下来的结果是:我们的项目解决小黄第一年的学费,后续三年的学费由舅舅和外婆各负担一半;小黄爸爸负担小黄前两年的生活费,每月800元,后两年小黄得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费。
小黄的眼睛里充满了失望和破碎感,让我们这些暗访的工作人员也瞧着不忍。我赶紧把小黄唤出来,悄声商量:“先答应你父亲的安排吧。去了大学,若有困难可以办无息贷款。你还可以争取奖学金,找一些勤工俭学的岗位,最后两年的生活费一定会有的。”
三
小黄如愿以偿,念完了书,又在乡镇文员的岗位上待了两年,非要辞职出来开饣它汤店,继母听了都有点生气——徐州靠近山东,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家长们都觉得孩子念了大学,最好能在公家单位里找一个体面的工作,钱多钱少倒在其次。此时此刻,继母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家长了。继母数落小黄的时候,爸爸依旧坐在小板凳上抽烟,不发一言。
过了几日,小黄正在即将开张的小店里砌灶台,佝偻着背的爸爸赶来了,小黄心中不免一凛,以为他又要来说自己有先见之明,当初就不该让小黄去念大学。谁知,爸爸来了以后,只是帮小黄刷了两面墙的乳胶漆,临走,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匆忙将一卷纸钞塞进小黄工装围裙前面的大口袋里,叮嘱他:“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那卷纸钞,多数是20元、50元的,还有薄薄一叠100元的。小黄一下子热泪盈眶。他明白,那是爸爸从前做麦客的收入,恐怕是他藏在哪个砖缝里的私房钱。在山东和河南,近些年只有麦客的收入才用纸币结算,那些纸币上凝结着烟草、汗水和麦子被太阳晒蔫时特有的味道。这一大卷纸币散发的难以言说的复杂气味,让小黄不由自主联想到爸爸左右为难的一生:他的左侧,是亡妻和腿脚不灵便的大儿子;他的右侧,是泼辣强势的现任妻子和永远只与妈妈亲的小儿子。而他站在中间,如此孤独又不安。
小黄摩挲着那些微微毛边的纸币,前所未有地代入了爸爸的一生。在那一刻,小黄终于理解了他的辛苦和不得已,以及他在老年将至之时的孤独。
四
小黄开了饣它汤店,还意外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姑娘是附近一家企业的文员,经常到小黄的店里来喝饣它汤,一来二去就跟他熟了。女孩外向且主动,见小黄店里忙不开,就会去后厨洗碗,也会帮小黄洗麦仁、切豆腐丝。姑娘还问小黄:“为啥不买一个电动打蛋器呢?那样会省力很多,可以把几十个蛋一起打了。”
小黄笑了:“你不懂,饣它汤的蛋液不能打得过于均匀,蛋清和蛋白似乎混合了,又没有完全混合,这样,饣它汤冲进去,浮起的蛋丝才有多种口感。”姑娘后来就不打蛋了,经常一大早就进后厨,仔仔细细洗过手,帮小黄扯鸡丝。暗示到这个份上,小黄再不能装聋作哑,这天早上,他在姑娘面前来回走了一趟,特意夸大了自己跛行的程度,问:“我这个样子,你父母会同意吗?到时候你夹在我和你父母之间,徒增痛苦啊。”
果然,姑娘回家摊牌,说了小黄的事,但隐瞒了小黄的腿疾。父亲当即出言反对,理由是舍不得姑娘一辈子都过凌晨3点半起床的日子。姑娘小声辩驳:“小黄不会让我起这么早的。他什么苦都自己一个人咬牙承受,我想帮帮他……”
姑娘不知道的是,老两口特意选了她出差的日子,接连三天去喝饣它汤。老两口观察到很多女儿没有提起的内容:小黄有轻微的跛足,还有个老太太经常来帮他的忙。从老太太与食客的对话中,可知她是小黄的外婆。小黄早已没了妈妈,现在,爸爸又得了糖尿病,重体力活是一点都做不得,连摘桃摘梨这样的零活儿也很难干得动了。无奈之下,他的第二任老婆只好到苏州服装厂当缝纫工,活计很忙很累,一年只能回来两趟,加起来也只有十几天。
外婆愤愤地说:“她从前对我外孙那样苛刻,恨不得不让我外孙念大学,现在咋样了?她也没活成富贵闲人啊。”
姑娘父母互使眼色,心弦一紧,倒是小黄出来劝阻外婆:“陈年旧事就不提了。林阿姨也不容易,全家就靠她撑着……”
隔天,再来喝饣它汤的姑娘父母又关注到一个细节:到了上午10点,小黄必要把店铺交给隔壁小老板看管几分钟。他们注意到,小黄总会拿出一个带盖的青花大碗,在碗里放入鸡丝,冲一碗加料饣它汤,加盖,用小提篮提着,往外走去。
姑娘的父亲拔腿跟上小黄。小黄朝着100多米外的中学大门走去,他走得又快又急,一直走到距校门10多米的铁栅栏处。
不到两分钟,下课铃响了,一个瘦高单薄的男生朝铁栅栏这头跑来。小黄赶紧将大碗隔着栅栏递给他。穿校服的男孩转着碗、吹着气,喝着饣它汤。栅栏里外的两个人一言不发,却有种无声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流动。接着,里头的男孩把空碗隔着栅栏递出来,小黄伸出手,鼓励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姑娘的父亲心中又是一动,他发觉,男孩与小黄长得颇有几分相像。
小黄没有想到,自己的恋爱从这一天开始峰回路转。他跟我讲了实话:“一直到开店之前,我都觉得我爸、继母、我弟,没有一个人对得起我。可是那天,我爸塞给我的那卷钱彻底打破了我的戒备。我终于知道,一家人就像饣它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麦仁里有鸡汤的味道,花生里有豆腐丝的味道,熬到后来,谁也离不开谁。从前,我委屈得不行,可要是站在我弟的角度,他就容易吗?”
竹筷子打鸡蛋的声音清脆又悦耳,大勺子搅动汤羹的声响含混又惆怅。是的,小黄说得对,爱与怅然、恨与牵挂,人生的百般滋味都是搅在一起熬煮的,到最后,哪儿有那么泾渭分明?不妨把心头的酸意放淡一点,再淡一点。
(《读者(原创版)》2025年10期[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