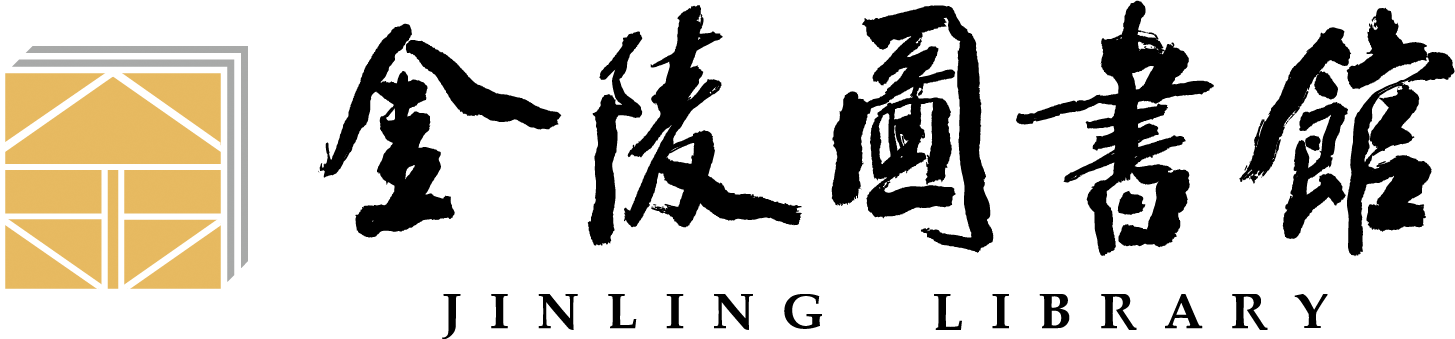![期刊架位号[5746] 期刊架位号[5746]](./W020251112556915415163.png)
冉景丞:贵州思南人,现居贵阳。
大学毕业后我到黔南荔波县工作,领导们非常热情,那时候的荔波还很偏僻很落后,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小县城里也算得凤毛麟角。领导本人也是老牌大学生,已经在荔波工作了几十年,知道大学生到这穷乡僻壤工作不易。单位同时分配来几名大学毕业生非常难得,做领导的多了几分骄傲。
领导邀请新入职的我们到他们家做客,说让我们去学吃一种特殊的美味——臭酸。我很好奇,什么好东西会叫这么一个名字,于是,当领导在炒臭酸的时候我还凑过头去看,对于好吃的人来说也想学学不同美食的做法。
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臭酸”,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而且是以一种“美食”的身份堂而皇之端上餐桌,觉得非常奇怪。榴莲虽然臭,但人家很甜呀,这“臭酸”又臭又酸还能是美食?
锅里的油烧得滚烫滚烫的,开始冒起青烟,领导手里端着一盆黑乎乎的东西,随手倒进了锅里。随着一阵白烟冒起来,整个屋里一下子臭气熏天,那种臭臭的气味似乎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真不好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没有憋住,一下子打了几次干呕,差点就吐了出来。领导看到我那狼狈的样子,有些尴尬地说:你不知道这东西可好吃了,闻着臭吃起香。
端上桌,我迟迟不敢下筷子,看到大家都吃得很香,甚至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兴奋,我才试着去品尝。说实话,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这东西的外乡人来说,闻着那特别的气味依然感觉到是一股恶臭,臭得想要放弃好奇心,放弃品尝人们心中的“美食”。最后还是扭不过同事们的劝说,我小心翼翼地挑了一点点,还是觉得恶心,没敢多吃。
没过多久,一个同事家办喜事,桌子摆了几大屋,菜也剩下不少。于是大家把剩下的那些菜收集起来,说要拿来煮臭酸吃。我当时嗤之以鼻,想想这些吃剩的东西,会做出什么好吃的味道来?原来人们心中的美食,不过是这样的残汤剩菜。我心中虽然这样想,却没有说出来,怕驳了同事们的面子。
这一次我学聪明了,他们煮臭酸时我没有去参观。由于自己没有煮饭,而且也不好意思反对同事们的提议,只好去凑热闹。本以为会有其他菜,吃一点蒙混过关算了,但没想到这次更特别,一大群人端着饭碗直接围着一个火炉,火炉上炖着一个大大的铁锅,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儿,向外散发着那种特别的味道。看上去油很多,还有些青绿的蔬菜,感觉是牛皮菜、红薯尖。里边还有翻滚的豆腐,一些肥肉、大肠。想想还是忍着吃吧,吃一点点、意思意思,别让别人看出我的胆怯。另外,我也觉得应该去试着尝试,毕竟今后说不定这样的情况还很多。
看很多人都吃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也挑起一些蔬菜放在嘴里,你别说,这东西还真就是可以下咽的。有了这一次的“进步”,在有人再提议吃臭酸的时候,我就不再那么反感了。
没过多久,又是一个被邀请吃臭酸的日子,而这一次我更大胆了些,不但吃了其中的蔬菜,还尝试吃了肉,吃了豆腐,还有大肠。奇了怪了,这一次不但没有反感,还觉得味道不错,真就有了“津津有味”的感觉。
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说起聚餐,吃别的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只要约起吃臭酸,倒来了兴趣。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没有什么规规矩矩、客套礼节,就这么随意地围着那一锅臭酸大快朵颐,有时候我们还就着臭酸喝起酒来,没完没了地推杯换盏,谈天说地。大家也不在乎那身上留下的浓烈气味,只不过还是会记得,吃完臭酸以后出门,还是得赶快去洗个澡换个衣服,要不然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自己吃了一顿臭臭的东西。
不知为什么,吃过臭酸的人都会上瘾,久了不吃还真有点想吃。
有一年,一个曾经在荔波待了多年的上海知青回荔波探亲,在他要回上海时,当年在荔波当过知青的同伴,纷纷表示想念荔波臭酸,希望他能带一些回去给他们解馋。
那时候没有高铁,也坐不起飞机,煮好的臭酸断然是不可能带到上海的,不光占地方,等到路上颠簸几天后拿到上海,恐怕就不仅仅是臭酸的臭味了。那只能想办法带一些“臭酸母子”到上海,再找个地方想办法去煮。
知青小心翼翼地将臭酸母子装在一个缸子里,用胶带将盖子严密封闭,再缠几层塑料膜,然后小心地放在行李包里。
火车从贵阳出发,一路经历了将近两天的时间,都没被发现。就快到上海,火车突然来一个急刹车,放在行李架上的行李从架子上掉落下来,装着“臭酸母子”的缸子也一下子滚落出来,盖子砸开。那恶臭的臭酸母子从缸子里流了出来,整个车厢马上被浓烈的臭味所渲染。
别人不知道那个恶臭会与美食扯上关系,只有知青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觉得都快到上海了,这就这么打倒了,回去没办法向知青同伴们交差,于是很吝惜地用手想把臭酸母子重新捧起来放回缸里去。这一动作马上引来了整个车厢人的反感,以为那是一个疯子,有人马上去找乘警,想要把这疯子抓起来,免得他害人。他们向乘警诉说:这疯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那些便便,还用手在那里搅和。
乘警来到车厢,果然看到这一幕,一下子果断地将知青按倒在地,抓将起来。那知青觉得非常委屈,说“你们为什么抓我?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所带的臭酸母子,一种美食的引子,打倒了,我想把它收集起来。”
车厢里的人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心想,谁会吃这么个东西?“把这个疯子抓起来。”无论知青怎么解释,不管是乘警还是乘客都不相信,只是纷纷要求把知青抓起来,免得他伤人。
满手污垢的知青被带到了乘警的办公室,弄得乘警这里也是恶臭不止。乘警嫌弃地丢几张纸给知青,要求他将手上的脏东西擦掉,然后开始审讯。知青一遍一遍地解释,“当知青时吃惯了当地的一种美食,这个是臭酸的引子,要用这个来煮菜,那味道好极了。”乘警怎么听都觉得他表达得清清楚楚,也不像是疯子。知青只是认真地说着自己的故事,乘警捂着鼻子再次打量了粘在缸底的那些脏乎乎的东西,实在不敢想象这东西可以入口。知青一再说这只是引子,等它煮出来了就不臭了,味道好极了。还用手指轻轻的蘸了一些臭酸母子放在嘴里,表示真的可以吃,吃给乘警看。
就这么闹了一个大乌龙,臭酸母子没带成,还引起了笑话。故事很快传回荔波,人们对臭酸的“认识”又深了一层。
曾经在荔波长大的一个青年,因为父母工作调动,一家人搬离了荔波,搬去贵阳。有一次小伙子要去荔波出差,家里人突然回忆起那臭酸的美味来,于是要求小伙去带一些臭酸母子回来,煮上一锅给全家人解馋。他们深知这臭酸的气味无敌难当,于是悄悄地准备好食材,在家里关门关窗悄悄地煮将起来,那气味太浓烈了,没办法,只好打开抽油烟机。于是很快整个楼道里开始熙熙攘攘,大家都在找、都在问“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下水道堵了”。连物管也来一家一家地敲门。
在家里悄悄煮臭酸的那家人躲在家里不吭气,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人家知道是从他们家里传了出来的。等保安找了一圈没找到,他们在家里已经偷偷吃饱,感觉到非常满意。这时候小伙子的姐夫下班回来,一打开门闻到这么浓烈的臭味,一下子转身便跑,一个星期都不敢回来。
这样的事不光是在贵阳发生过,还有一个客人将臭酸母子带到了广州,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煮吃,被举报当成疯子抓了起来。
要说这特殊的味道,可能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明白。但是也有些不一样的,有些人第一次就对这个臭酸情有独钟。
有一次外面来了很多领导,在单位的食堂搞接待。当天几个人已约好要煮臭酸吃,而且臭酸已经煮在锅里,那臭味是掩不住,搞得楼道里都是那味。领导们是断然不会吃这种东西的,就在隔壁的房间给领导们准备了满桌子的美食,由主要领导去陪同,其他职工都跑去吃臭酸。结果其中有一个美女领导居然跑到这边来,说要品尝一下大家正在吃得津津有味的臭酸。这一品尝不打紧,美女领导一下对这种味道着了迷,和大家一起大快朵颐。
绝大多数到过荔波并在小城生活过的人,都会迷恋这臭酸的味道。当然也有人觉得总是不能适应,永远也无法接受那道“特别美食”。其实如今吃臭酸,味道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当年那臭酸独特的味道似乎有些淡了。也难怪,当年食物短缺,人们将剩菜收集起来,用这臭酸一煮,再加一点大肠和蔬菜之类的东西,那味道果然很香。但今天人们对剩菜已不再青睐,即便要吃臭酸,得买来新鲜的食材,用臭酸母子来煮。人们慢慢发现,这新鲜食材直接煮总是没有隔夜的剩菜好吃,于是乎不管是豆腐还是肥肉、大肠之类的原料,最好是头一天买来发酵一宿,第二天再煮,强烈的味道才能上来。
我离开荔波十几年了,还真就怀念起臭酸的味道来。但如今吃臭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几次嘴馋了想跑回荔波吃臭酸,始终没有如愿。主要原因是煮臭酸的条件越来越少。今天多数人都住高楼,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小院儿,没有了在露天里煮臭酸吃的环境。而住在楼房里的人家虽仍喜欢吃臭酸,但谁家都不愿意在家里煮臭酸,因为那味道果真难以消除,至少一个星期都能感觉到臭酸的威力。
臭酸好吃,关键在于臭酸母子。据说那臭酸母子越臭,煮出来的臭酸越可口。会做臭酸母子的人并不多,就那么几个,都是他们做好了,别人家想吃时来他们家里讨要一些去煮。据说这臭酸母子的制作工作也较特别,原料也很多,还要用上大麦、凤仙花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这算不算“非遗”,会不会过时,会不会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变慢慢就失传了。
还没写完,口水早已经流了几遍。
油饼妇人
思南中学,前身是1904年4月创建的“思南府官立中学堂”,经历了“八县联立中学”“省立第七中学”“省立思南中学”等阶段,1951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定名为“贵州省思南中学”,该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说是百年历史一点都不为过。作为省级重点中学,思南中学曾经有“进了思南中学,一只脚就进了大学”的说法。
即使是在到思南中学上学前,我对思南中学也并不陌生。毕竟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思南中学毕业的,他们在学校读书时,我也曾跑进去看过,对那古老的校园多少有些印象。整座学校建立在坡地上,总是一段接一段的石阶,长长的木结构瓦房,有几幢还带些雕梁画栋的感觉,据说那曾经是文庙,那柱子比一个大人的腰都粗,还是什么马桑木的。也想不通,现在所能看到的马桑都是灌木,根本长不高,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马桑树?房屋之间点缀着几株苍翠的古树,好像是榆、柏、梧桐之类,最多的还是柏木。最为特别的是那个“无水三拱桥”,我总在想,既然无水,为什么还要在那里修三座拱桥呢?
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且家境贫寒的人,并没有想过要去思南中学读书,甚至就没有过什么理想。实在要说理想的话,最希望的就是尽快长大成为劳动力,或者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摆脱贫困的境地。那时候农村最有机会接触的拿工资的人就是老师,那也是乡村里最受尊敬的文化人。于是我一门心思想去读师范。但那时候的师范可不容易考,一方面我对自己的成绩没有底气,另外一方面我的个子矮小,站在黑板跟前踮起脚跟也才勉强够着黑板。而师范毕业是要当老师的,写黑板字需要有一定的身高,因此只能放弃幻想。
我虽然也报名考思南中学,但对考上思南中学并没有抱太多幻想。意外的是我竟然被思南中学录取了!后来据说是那一年正好改革招生方向,专门从农村招收了一批年龄相对较小、学习成绩又较好的学生用来作为试点。而我正好归到这一类人群,就这么进入了思南中学。
等我上思南中学时,校园与我记忆中已经有些差别,新修了教室和操场,院子里也增加了一些绿植。上高中的新鲜感还没有褪去,就迎来接二连三的打击。我初中时根本没有认真学习过英语,而城里的孩子们都多少有些英语成绩,尽管老师讲得很认真很吃力,我却听起来像是在听天书。本以为自己的数学成绩比较好,但真到了高中,那些公式、原理搅得我脑袋发晕。还有语文、物理、化学,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的班主任是郑培珍老师,她是上海人,曾经的上海知青,口音还没有完全被思南话同化,那奇怪的腔调倒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郑老师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头卷曲的头发,圆圆的脸上大多数时候都带着笑容。她讲课讲得很认真很投入,每当讲到兴奋处也会做出一些夸张的表情。若是发现有学生开小差没有认真听讲,她会心疼地指着学生说:“你这个鬼崽崽呀,家里送你来读书容易吗?怎么不认真学习呢?”真有学不懂的学生,她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学生弄懂为止。
郑老师和她爱人都是上海知青,都在思南中学教书。据说她的爱人陈老师更牛,数学、语文、化学、物理都很在行,只是没有直接教过我们。陈老师与郑老师截然不同,不苟言笑,任何时候都是一张严肃的脸,我们远远地看到时甚至有点想躲开。他们的两个孩子比我们稍小一些,好像一个在上初中,一个在上小学,但郑老师的精力似乎主要都在我们这些农村娃身上。我们班同学都比较喜欢郑老师,当然也怕她,犯点小错被追问时都一定会避开她的眼睛,尽管知道她高度近视不会看得清同学的表情。
虽然我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有些家境好一点的可以穿一身光鲜的衣服,而更多的孩子都穿得很朴素,一年到头就那么一两身衣服,有些衣服上还有补丁。郑老师不会嫌贫爱富,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样的热情。
学生的主要精力就是学习,除了上课就是看书、吃饭、睡觉。从教室回到寝室总要路过一棵大树,好像是一棵榆树还是槐树,已经记不清那是一棵什么树了。树下时常看到一个卖油饼的中年妇女,个子高高的,脸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油光水滑的红润,身体有些像郑老师那样的富态。具体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不清楚,只是同学们当面喊她做“孃孃”,背地里都叫她“油饼妇人”。她有时候撑一把伞,有时候直接就一个摊。那摊也简单,就是一只背篼上面放着一个簸箕,簸箕上铺着一层棉垫,棉垫上再铺上一层塑料布和毛巾,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叠油饼。油香味从盖在油饼上的白布中传出来,穿透空气,钻入鼻孔,总惹得人垂涎欲滴。有不少的同学在经过的时候会停下脚步,买上一个油饼,美滋滋地边走边吃,对于我这种没有钱的学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快速离开,免得被油饼的香味勾去了灵魂挪不动脚步。
那油饼的香味像是着了魔一样,总是在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即使逃进了寝室,那气味好像也会从窗子飘散进来,勾引着我的嗅觉和味蕾。于是我对油饼妇人有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恨,最恨的不是因为她的油饼香味勾引了自己,而又没有钱去购买她的油饼。最恨的恰恰是她那富态的身躯,居然敢与我们的郑老师相似。郑老师可是神一样的存在,油饼妇人算老几?
这些都只敢在心里暗骂,不敢让油饼妇人知道,也不敢在其他同学面前表露。恨归恨,在有机会的时候实在扛不住馋虫的勾引,还是会把从家里拿来的口粮包上一小包,拿去换一张油饼吃。油饼妇人对那些经常买她油饼的人很热情,对路过的老师们也客客气气,尽管很少看到有老师去买她的油饼。对于我们这种想用米去换油饼吃的她也不拒绝,但我们自己却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一样,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口袋递过去,等待她检查完米的质量,拿上油饼飞也似的就跑开,生怕被人发现自己用米去换油饼。
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高三,我们的教室也从教学大楼搬到了桃源教学楼。桃源教学楼是一栋老房子,是砖瓦结构的两层木楼板房,楼梯也是木板的,已经磨损得有些坑坑洼洼,踩在上面“哐哐”作响。我也早不像刚入学那样腼腆,对校园的情况早已很熟悉,开始有些小调皮。对学习也不再像之前那么着迷,但是看到其他的同学都在努力,自己也会装腔作势“努力学习”,只不过是想赢得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好感。
下了晚自习,学生们从教室里鱼贯而出,也有几个不想离开教室的,继续在教室伏案看书。他们不怕学校会统一关灯,书包里藏有一个小小的油灯,那是在教室熄灯以后继续学习的有力工具。我很少那样努力,除非拿到了一本被限定还书时间的好书。
从桃源教学楼走出来时,远远就能隐隐约约嗅到油饼的香味。还是在那棵大树下,一把伞一个油饼摊,以及守在摊前的油饼妇人。边上的路灯杆下有几个同学在看书,那路灯几乎通宵亮着,是这校园里最明亮的地方。当有人路过油饼摊时,油饼妇人就会习惯性问道:“要油饼不?热乎的。”
有几位同学围在油饼摊旁边开始买吃,对于我这种口袋干瘪的穷鬼只能快速地逃离,在心里啐上一口,还会暗暗地骂上一两句。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晚上卖出的油饼那味道更香,香味飘得更远。若是冷天或是雨天,回到寝室就蒙头大睡,防止继续闻到油饼味。而在热天,万不敢在寝室待着,总要尽快拿上脸盆和毛巾冲到学校外面半坡上那个水井去好好地冲一个凉,顺便冲洗干净跟着飘过来的身上的油饼味。说来也怪,哪里来那么多“有钱人”?每次从外面冲凉回来,油饼妇人都已经卖完收摊,这倒让自己睡得更安心。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有电视的人家算是富裕之家了。但像油饼妇人家那样不仅有电视还有一个宽敞的小院子的人家,更是了不起的“富豪”。记得当时正好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听着“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主题歌声音,总忍不住循着声音去找电视机所在地。也是因此才发现原来油饼妇人家有台彩电!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家将电视搬到小院子来,与没有电视的左邻右舍一起欣赏。
小院子里挤满了人,这些人或者是油饼妇人家的熟人,或者是那些经常在那里买油饼吃的人。像我这种很少有钱买油饼,甚至用米去换油饼的次数都寥寥无几的人,是肯定没有资格能进入小院子里看电视的。她家的院墙大约有两米高,下面三分之二部分是实体墙,上面三分之一部分是用砖交叉砌出的花格子,这就给我们留了机会。我们找来几块砖头或者木板或者石头放在高高的院墙外,垫在脚下伸长脖子就可以从那院墙的孔洞中去欣赏电视情节了。最可恶的是,有时候好不容易找来了砖头或木板,待踮起脚尖望进去时,却被人头遮住了视线,或者电视机居然换了位置,从墙外根本看不见,也就听听声音看了个寂寞。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油饼妇人家在故意显摆,或者是想用这种方法与人搞好关系,反正在我们看来,调换方向让我们空欢喜就是恶作剧。于是有同学想到了报复,居然利用高中物理所学的无线电知识,弄上一个线圈加上二极管三极管之类的东西,制成一个简单的“信号干扰器”。只要在他家附近不停地按动干扰器,那电视上就会出现阵阵的雪花点点。心想,你让我们得不到看,我们也让你看得不安宁。
我没有干过这样“刺激”的行动,不是因为我的心灵多高尚,而是没有钱去买那些电子小元件。与其拿钱去报复,不如拿到书摊去多看两本书。遇到得不到电视看的情况,只是在心里暗暗的骂上几句,但每当见到油饼妇人时,总会腆着脸讨好似的上去喊一声“孃孃”。期盼着下一次在他家墙外看电视时不会被赶走,或者又把电视机转了方向。
高三下学期本来是学习最为紧张的时候,郑老师却调走了,调到了余杭中学去了。我们想,不是因为她想离开我们这些学生,而是余杭离她的家乡近一些,她出来了一二十年,她的父母也一定很想她。看着那大车来帮她家运家具,看着郑老师一家人上车离去,心中一阵阵地痛。几次泪水差点就要流出来,竟是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同学们对郑老师的思念很快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抗拒所有来接替郑老师当班主任的老师!甚至对那些试图来说服我们的老师充满了敌意,以至于好几个老师都被我们班同学气跑,甚至气哭。一向与同学们关系不错的教外语的张老师、教化学的古老师、教物理的杨老师都拿我们没有办法。反而是跟我们班没有多少交情的田老师,狠狠地骂了我们一顿,甚至提出可以与同学单挑,才算把局势控制下来。
尽管田老师已经是我们的新班主任,尽管田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异常卖力,但还是没有办法平息我们对郑老师的想念。奇怪的是,几次梦见郑老师给我们上课,但一转身却变成了油饼妇人的样子。从梦中惊醒过来,恶狠狠地在心里暗骂上几句,她凭什么?
时光依旧,日子依旧。还是会在晴朗的时候跑到油饼妇人家的墙脚下去听听有没有放电视的声音,或者找几块砖头来踮着脚尖往里窥视,看有没有好看的节目。直到高考完毕,油饼妇人的摊子依然摆着,那油饼的香气依然飘散在空气里。
我离开思南中学到东北去上大学,毕业后也没有回到故乡工作。我再次踏入思南中学的校园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桃源教学楼已经不在了,学校的好多老房子也拆掉新盖了,教室比当初舒适了很多。我问学校的老师,年轻老师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油饼摊的印象。
当年那棵大树还在,我的记忆也还在,只是树下已经没有油饼摊,也没有了油饼妇人的身影。
(《南风》2025年4期[5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