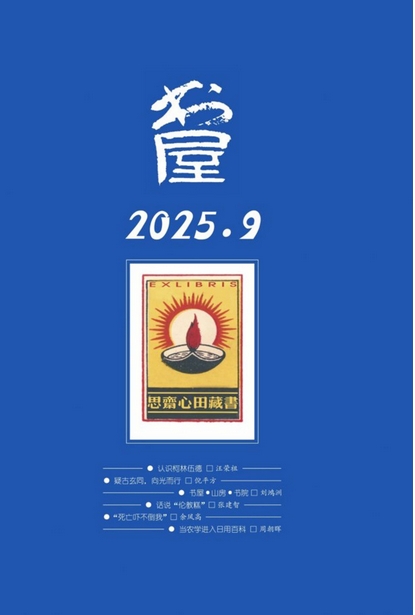
父母去世后,我在整理旧书时找出不少学生时代的藏书,其中就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购读的《家庭日用大全》《花镜》《少年科技制作》等书。
1980年暑假,母亲参加在厦大举行的高考监考兼评卷工作,得了一笔名为“防暑降温补贴”的奖金,给了我五元钱买暑假课外书,我迫不及待到书店将惦记很久的《家庭日用大全》《花镜》等书买下。顺便提及,《家庭日用大全》标价一点四元,这在大学讲师月薪才七八十元的当时并非小数目。此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城市生活日用指南,举凡日用品保养、洗涤保管衣服、裁剪、刺绣、编织毛衣、烹饪菜肴、打造家具、盆栽养鱼、病伤防治、美容养生至家庭琐事处理等,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从出版印数可见一斑:1980年4月初版后,紧接着在7月就重印,印数一下就上了五十二万册,到当年9月就进行了第八次重印,印数达到八十五万册之多,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当之无愧的超级畅销书。遥想当年,国家拨乱反正、百废俱兴,这类书的热销似乎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2023年,我走访福建南平的“建本文化展览馆”,接触到大量明代建阳民间刻印的日用类图书,恍然想起家里尘封的《家庭日用大全》,找出翻读之下,感受到一种古老知识体系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的历史传承。
从精英文化到大众读物:日用类书之源流
日用类书是类书的一种。所谓类书,是对群书中的各种知识和各种资料进行分类汇编,以便翻阅检索与使用。类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即所谓“包罗万有”;二是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也就是“随类相从”。这两个特点很像近代西方兴起的百科全书。
我国早期的类书主要有三种:帝王御览、文人獭祭辞藻和士子应举指南。虽然“类书”一词直到欧阳修编撰《新唐书·艺文志》中才出现,但其起源却远早于此。曹魏时期曹丕敕撰的《皇览》是类书之祖。南北朝时期有《华林遍略》《科录》等多种类书问世。隋唐之际,官修类书风气颇为浓厚,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和《艺文类聚》等,主要供文人词臣写作诗文参考。垂至两宋,随着文治时代的到来和图书刻印技术的发达,类书撰写和出版形成潮流。宋代官方修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规模宏富,囊括万有,文人士子无不受其泽惠。在官修类书的影响启迪之下,民间私撰类书之风兴起,出现了如《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古今源流至论》《玉海》等面向科举士子的类书。
南宋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生产达到历史高峰,带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同时,南宋政府大力兴学,文化教育相对普及,识字人口远超前代。各种社会需求互相激荡,广大民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需求。于是,一种新型的类书在民间悄然出现并渐成潮流,这就是后世学者通称的日用类书。其中所载的内容不再是传统类书所包含的诗文典故、官场指南或科举应试攻略,更多的是涉及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诸如居家日用、游艺消闲、通俗文艺等,以满足世俗百姓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其代表作品有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温革的《分门琐碎录》等。与以往那些面向皇室、官府或士大夫阶层的类书不同,这类日用类书开始关注城乡居民的需要,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识技术分门别类,汇编刊载,以便查询使用。到了元代,日用类书朝日常化、实用化趋势更为明显。元代中期出现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载内容涉及家居日用、官场应酬、市井营生、休闲娱乐和书房清玩之类,囊括民间居家日用所需的各种知识技术,如农桑、医药、饮食、穿戴、路途、气象、历法、赋税、刑律、算术、尺牍、风水、诉讼、劝善、礼法等。或采自典籍,或来自民俗俚语,或出于经验心得等。
从读者对象来看,宋元时代的日用类书基本上还以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主,如陈元靓的《事林广记》载有大量有关文房、词章、文籍的内容;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文房”“为学”“仕官”“为吏指南”,则明确了是以科举士子、世家子弟或各级政府衙门的官吏为主要读者对象,虽有涉及耕织、工商之类的日用内容,但比例很小。上述读者受众群体的狭窄,导致这类书籍的传播范围很小,仅限于在上层社会流传。到了明代中期,类书的读者面向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日用类书热:明代知识通俗化背后的思想哲学
明代是我国古代类书出版的黄金时代,而民间日用类书则占了很大的比重。
从内容上看,明代日用类书可谓包罗万象。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出版研究》一书统计,目前在各类书目文献中能看到的明代日用类书,仅在万历年间以后出版的就超过两百种,如果加上那些散佚或没有被记录的,数量更为庞大,完整存留至今的亦有不少。2004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由酒井忠夫监修的《中国日用类书集成》十四卷,收入晚明出版的日用类书六种,其中大部分是明代建阳坊间的刻本。2011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十六卷,收录明代各种书坊刊刻的日用类书四十四种,是目前明代日用类书集刊之最。这些类书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在版式上大致以福建建阳刊刻的同类日用类书为标准,上下两截版式,图文并茂;二是书籍具有实用性,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中,可供活学活用;三是承载的知识技术具有多样性。类书内容涉及面很广,如署名葆和子辑录的《新刻增补士民备览万珠聚囊不求人》一书,内容就包含天文、地舆、人纪、官品、诸夷、法律、四礼、医学、卜筮、星命、相法、文翰、书信、民用、诗对、武备、农桑、侑觞、养生、解梦、算法、种子、八谱、仙术、笑谈、杂览等二十六门,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几乎涵盖了当时城乡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代日用类书的繁荣,有赖于高度发达的印刷技术的保障。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明中期兴起的大众文化热潮。日用类书在明朝中期以后的空前繁荣也是市民文化兴盛的一个标志,明代出版的日用类书中除了日用知识技术以外,还有大量通俗小说、笑话和趣谈的文本即是例证。此外,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大大促进了这些日用类书的流通。刻字技术的改进使得同一块雕版的使用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减少了损耗,从而降低了印书的成本,而销售渠道的畅通也使得书的价格变得相对低廉。从农学知识技术的传播角度看,这类面向一般民众的农学读物,因价格低廉、内容简明易懂,比起《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面向知识精英阶层的大部头著作更受欢迎。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农学知识技术在民间的普及。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反响,因此明朝中期兴起的通俗文化热潮,某种意义上是对主流正统文化的冲击。宋代以来标榜的“存天理,灭人欲”价值观,以及提倡秩序与尊崇的程朱理学开始走向衰落;强调人的自我价值和心是万物主宰的阳明心学逐渐发展起来。阳明心学重视从日常事物中格物致知,倡导“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认为学问不应该由圣贤所垄断,而是“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真理,将居家日用视为最重要的修炼功夫,庶民百姓也能“超凡致圣”。如此,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反映百姓日常需要的图书得到进一步关注,面向普通百姓的营利性书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当农学成为系统化的生活知识
晚明江南出现了大量日用类书,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这些类书借鉴唐宋类书的编纂体例,内容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类书主要是为适应四民百姓,特别是针对农村农民的日用生活需要而编写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的四个阶层中,农民不仅人数最多,分布也最为广泛。农业一直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支撑国家政权运行的最基本保障,农业也被视为“本业”受到统治者推崇。在此背景下,农业知识技术大量进入日用类书中,成为一种系统化的生活知识。
农业知识进入日用类书并非自明代始,成书于南宋末年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中,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农桑知识的篇章,名为“农桑类”,介绍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及养蚕缫丝的知识技术。此外,还有“花果类”和“竹木类”两篇,分别介绍论述花卉果木和经济林木的种植技术。陈元靓将农业知识编入日用类书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不仅收录农业知识,而且包含的内容扩大为种艺、种药、种菜、果木、花草、竹木六大类,占了全书内容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关大田作物的栽培和管理占了很大比重。
农业类日用类书是明代中晚期日用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知识技术主要以“农桑门”的专题出现在类书中。在收入《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的四十四种万历年间以后出版的日用类书中,明确载有“农桑门”的类书有近一半,个中更有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日用类书,如《便民图纂》《多能鄙事》《致富奇书》等就是明代颇具代表性的民间日用生活百科全书。
《便民图纂》是明代流传最广泛的百姓日用类书。作者为弘治年间的地方行政长官邝璠。本书以农村农事活动如务农耕获、桑蚕树艺、牲畜牧养为主,旁及占卜祈穰、医药处方、养生调摄、园艺种植、饮食制作等,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颇能满足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清初学者钱曾盛赞此书“凡有便于民者,莫不具列”。本书大约成书于十六世纪初,在雕版刊行之前就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后经江苏、江西、云南、广西、贵州、河北、福建等地的官府刊刻颁布,广为流布,在从明代弘治年间至万历中期的一个世纪内至少被刊刻过七次,是明代一大畅销书。
明代日用类书与全球性平民读物浪潮
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被销往日本、朝鲜、琉球等东亚汉文化圈。在大航海时代,有的还传入西方,受此影响,欧洲很多地区也生产出一批以日用家居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
日本在唐宋时期就大量从中国输入汉籍,类书以其工具性、收藏性、便捷性和派生性等特点受到欢迎。平安时代,萧衍敕撰的《华林遍略》和唐代的《初学记》等类书就传入日本,被皇家图书院奉为至宝,只有皇室贵胄才得以一览。江户时代虽然实行锁国,厉行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禁,但对于历法、天文、数学和医药等书籍却极为宽容,对这类书籍的搜集和引进也有政策有系统。福建、浙江民间出版的日用类书深受日本学界与民间的青睐。明中后期,福建刊刻的日用类书大量出口到日本,如《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书渊海》《五车万宝全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妙锦万用全书》等,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农书一样成为备受欢迎的汉籍。明崇祯九年(1636),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脱稿,翌年在建阳书坊刻印出版。该书本是总结明代前沿科技著作,但所载内容涉及农业、手工技术等知识技术,如谷类加工、衣物织染、制糖、制盐、酿造、铸造、制陶、造纸等。书商刻意将其包装成日用类书销往日本,在日本引发巨大反响,成为载入出版史的文化事件:《天工开物》先是以汉籍原著和手抄本的形式传播,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1771年,大阪“菅生堂”刊行了由汉学家江田益英训点的和刻本《天工开物》。训点是指古代日本人在诵读汉文时在原文旁加注读音与标点,使之便于阅读理解和记忆;和刻本的诞生使得《天工开物》在日本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根据农史学者数内清的研究,在江户时代,《天工开物》已经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直到明治维新前后还在大量出版。
江户时代中后期,随着庶民教育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升,明朝日用类书籍的受众进一步扩大,一些书商与学人合作,借鉴模仿中国日用类书的形式编撰适应日本国情的同类读物。据《江户时代庶民文库》一书的介绍,十八世纪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会,与庶民日常相关的家政类书籍很受欢迎,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民家丰饶重宝记》《俗家重宝集》《万宝智慧袋》《民家日用广益秘事大全》等。中岛良安受到明朝王圻所著《三才图会》的启发,创作了描述和图解日常生活的《和汉三才图会》,其中就包含了大量农业耕织方面的内容,成为江户时代长销不衰的书籍。而《民家日用广益秘事大全》更涉及城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农耕、蚕桑、园艺、算法、律法、赋税、医药、保健、烹调、商业知识、冠婚丧祭等。在编排目次和内容上,这些书与明代的日用类书中农业知识的体例极为相似。书籍的版面装帧和封面设计都仿照明代类书样式。为了防止盗印,很多书商在这类书的封面上都标注“千里必究”字样,这也是模仿明朝书坊刊刻的防伪防盗声明。锁国时期的日本人从中国日用类书这些“实学”著作中获得的知识技术,终于在十九世纪后开花结果。
随着世界海洋时代的到来,东西方的往来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日用类书还经由闽南海商传入西方,使得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与想象落到了实处。特别是伴随着印刷术的进步与庶民识字率的提高,在欧洲兴起的通俗读物浪潮中,很多地区也出现了以居家日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如法国在十七世纪初也出现了与日常生活知识技术相关的小开本简易读本,虽然制作粗糙,但因价格低廉和内容实用,成为当时乡间最普及的通俗读物。在十八世纪的德国,以解决家庭生计为目的的家政学著作颇为流行,其重点也是论述与农事相关的活动,是当时平民大众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
从“兔园册子”到学术殿堂
日用类通书迄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读物。如前所述,这类书籍是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生活指南,是面向庶民百姓的读物。而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这类图书,它呈现出的却是普通百姓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等,构成了普罗大众精神世界的底色。但在传统中国社会,此类书籍因其读者面向与刊印质量问题,多不受藏书家重视,也为主流学术界所不屑。
作为一种工具书,日用类书当然有其局限性。首先是缺乏原创性。博采群书、兼容并包是类书的一大特质,资料性与便利性是其所长,历代类书的编撰者都坚守着述而不作的传统,着意于文献资料的承袭与汇总,原创性则显得欠缺。其次是出版物质量问题。限于编撰者水平或执着于商业谋利等,很多类书存在着托伪自重、重复累赘、粗制滥造甚至是剽窃拼凑等问题,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明朝日用通书不被藏书家或正统学术所重,比如四库馆臣就视之为不入流的“村塾兔园册子”。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因书中有“华夷之辨”的内容,被乾隆斥为“离经叛道”,一度被列为禁书。
不过,“墙里开花墙外香”。与在国内受到冷遇成对比,日用类书很早就受到日本的关注。在对明代日用类书的研究上,日本学人也有祖鞭先著之功,江户时代后期的学者就将其作为研究汉学的重要参考。明治维新后,一些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更视之为古代社会生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的富矿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二十世纪初,东京大学的汉学家仁井田升注意到中国日用类书所载史料的独特价值,将系统收集整理的各种版本的日用类书运用于对中国法制史、教育史的研究,撰写出研究唐代法律的专著《唐令拾遗》,轰动日本东洋史学界。京都大学的汉学家历来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收集、挖掘与研究,借助精湛的学术素养,善于从一些不为人所重视的边缘性文献资料,如杂著、幼学蒙童课本、民俗等,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专攻中国近世文学的小川阳一从日用类书的视角研究明清小说,他将类书中的酒令、饮食、占卜与《西厢记》、《金瓶梅词话》、“三言二拍”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对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进而对明清通俗文学的发生、发展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以“茄鲞”款待刘姥姥,并对烹饪做绘声绘色的描述,唬得刘姥姥“只有念佛而已”。而茄鲞制作方法就出自成书于1744年的类书《农圃便览》,这道食谱又是源自《便民图纂》。显然,曹雪芹在写作这个章节的时候,可能参考了当时流行的日用类书。
明代日用类书对传统农业技术的研究具有独特价值。我国农史学前辈石声汉被誉为通用类农书研究第一人。新中国初期他就著文介绍《便民图纂》,对该书所包含的农业生产技术、食品制作、医疗养生、家庭日用品的制作维修、农业气象和占卜等传统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所需的技术知识进行详细介绍,引起学术界重视。现代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也是对明代日用类书进行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他收藏的数万卷古籍善本中就有近百种明清日用类书。他在《西谛书话》中对此多有论述,指出“研讨省会生活史者,将或有取于斯”。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便民图纂》影印本,就是以郑氏所藏的明万历于永清刻本影印出版的。
时代在变化,人们的阅读方式和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在改变。今天再重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家庭日用大全》,就会发现很多技术知识不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更何况是明清甚至更久远时期的日用类书。但蕴藏其中的史料价值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人将日用类书视为古代社会生活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的富矿。换言之,日用类书这类曾经被传统精英人士所鄙薄的“兔园册子”,逐渐登上了学术研究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