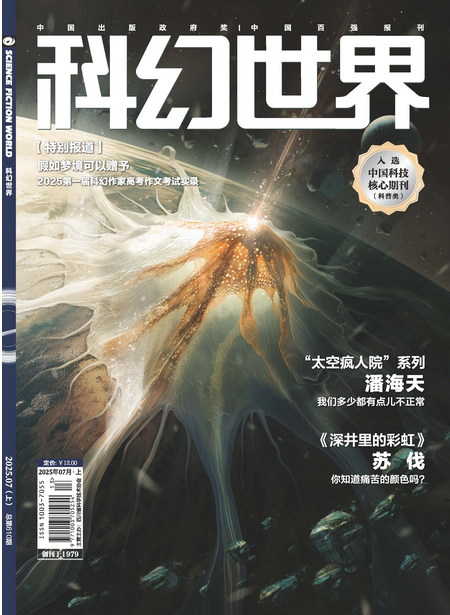
我离开蓬塔尔吉斯期间,布万库尔换了一名新管家。那位新女仆一口咬定她的主人出去了,可她根本是在骗我——我明明听见我那位朋友在走廊尽头实验室里高声说话。于是我也不客气,大声喊道:“布万库尔!喂,布万库尔!是我,桑布勒伊。就算你下了逐客令,但我能进去吗?”
“啊,亲爱的医生,真高兴又见到你!”那位科学家在门后头回应,“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和你握手,桑布勒伊!可惜有点小麻烦。我还得被关在这屋里半小时,现在实在没法开门。你先从客厅进去,到我书房里待着吧,麻烦你了。咱们隔着门聊也行,总比你站在门厅舒服点。”
我对这间小公寓的布局再熟悉不过。我可喜欢这间房子了,主要是因为住在里面的人。我们俩平时聊天常待的就是那间路易十五风格的客厅,虽然里面的家具初看上去华丽得过头,实际上又极其平庸,但我还是挺乐意再去一次的。布万库尔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位室内装饰大师(虽然实际上完全搞错了)。他闲暇时就喜欢钉钉子、锯木头、挂窗帘之类的活儿。在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看来,能够设计并打造出那些椅子和壁架,使之“能与一套真正的壁炉铁具相配”,也许不是他最显赫的荣耀,但也算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
于是我用饱含深情的眼光扫视了一圈这些可怕的仿制家具——一些木制家具是用模具压出来的,挂毯则虚假地冒充昂贵的奥布松挂毯1,但我压根没有感到震惊,因为这些丑东西我早看习惯了。不过,一进他书房,我就又一次被布万库尔那荒唐的虚荣心震了一下。他给书房搞了一个特别吓人的装饰。
为了让屋子显得更大,他用了障眼法,在把书房和路易十五风格客厅隔开的墙上安了一整块大镜子。那镜子伪装成一扇门,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给人造成了错觉,简直就像格雷万蜡像馆2里那些骗人的机关。那面大镜子直接立在地板上,为了更逼真,他还在周围挂上了一圈深酒红色的长绒窗帘——和那些挂在寡妇家门口的窗帘几乎一模一样。哦,那些窗帘啊!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他亲手做的——褶是他压的,鼓起的波浪是他弄的,瀑布似的垂挂也是他搞的,这位地狱般的室内装饰师,用那些带穗的绳子把它们绑成如今这副模样!我站在那恐怖的帘饰前,眼睁睁看着那些绳结把布料扭成了一团可怕的造型,整个人都说不出话来。
“喂,医生,”实验室的门里传来布万库尔压着嗓子的声音,“你过来了吗?”
“来了——不过我正欣赏你的装潢呢。你这镜子,太牛了!”
“是不是?帘子怎么样?我亲手弄的哦。你不觉得书房看起来超大吗?现在特别流行这种风格。我这书房,是不是挺有腔调的?”
确实,这屋子的“腔调”不是没来由的,但不是因为那些装饰性的家具,而是因为这房间本身就是隔壁实验室的延伸,里头藏着各种惊人的机器,形状奇怪、大小不一、材质五花八门,都是拿来做实验和演示用的。这间角落里的房间有两扇窗,一扇朝大街,一扇朝小巷。阳光洒进角落的房间,在硬橡胶、玻璃和铜器上洒下点点光辉,泛起粼粼波光。借着这些光,我能看到一些天平盘、圆盘和圆柱体。书桌上堆满了手稿,像是被灵感狂潮抛上去的一样。黑板上还有一道代数题没擦。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化学实验的味道,科学感十足,我赞叹道:“没错,布万库尔,老兄——你这书房,太有腔调了!”
“抱歉只能用这种方式接待你。”他接着说道,“今天是星期六,我的实验助手……”
“还是菲利克斯吗?”
“当然,还是他。”
“你好啊,菲利克斯!”
“您好,桑布勒伊先生。”
“我的实验助手,”布万库尔继续说,“问他今天能不能早点下班,明天他要出远门。我这实验又实在不能拖了。”
“所以这个实验是不是很厉害?”
“非常厉害,我的好兄弟。这是一系列实验的最后一步,应该能得出决定性结论。我肯定能搞出个大发现……”
“什么发现?”
接着,我听见了电磁感应线圈发出的嗡鸣声。有好几个线圈在运作,那种声音根据线圈的松紧程度不同,像蜜蜂或大黄蜂振翅飞行时的声音,它们一起嗡嗡作响,汇成一曲还能忍受的杂音交响乐。那该死的低音,在这个宁静的小城里嗡嗡作响,催人入睡,要不是外头的有轨电车时不时从大道上驶过,将一阵阵喧闹声传到楼上,我恐怕早就打起盹来了。电车的电缆就从我们房子窗前不远的地方穿过,甚至还有一个电缆支架固定在外墙上,就在实验室的窗户和书房的窗户之间。每次电车触到那个接点,就会蹦出火花。我百无聊赖地等着,靠这些火花提提神。同时,线圈仍在不停地嗡嗡作响,仿佛一个蜂巢在活动。几辆电车接连驶过,车轴咯咯作响。我一向喜欢计数,便顺势数了数。
“你们快结束了吗,布万库尔?”
“需要一些耐心,桑布勒伊先生。”菲利克斯声音模糊地回答道。
“顺利吗?”
“太顺利了。我们就快完成了。”
这几句话点燃了我极强的好奇心,我想冲进那扇门,亲眼看看那个首次出现的新现象,也想亲眼看看科学家在发现瞬间的神情。布万库尔之前就因为一系列新的发现,在“名人日历”上留下了不少光辉时刻。
座钟响了。我颤抖了一下——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能进去了吗,菲利克斯?”我哀求道,“我快无聊死了。这都已经是经过的第二十辆电车了,小兄弟,而且——”
我话没说完。就在第二十辆电车碰上接点的那一刻,一道火花蹦出,劈啪作响,亮得像闪电一样。紧接着,实验室门后传来一连串爆炸声,同时夹杂着一些不痛不痒的咒骂声。
砰!
“哎呀!”
噗!
“见鬼!”
啪!
“真该死!”
诸如此类。布万库尔咒骂的方式比较寻常,还没到亵渎神明的程度。
等他的骂声停下来后,他喊道:“全得重来!真是灾难!菲利克斯,我的可怜孩子,咱们真是倒了大霉啊!”
“到底怎么了?”我问。
我识趣地闭上了嘴。几秒后,我听见菲利克斯打开通往走廊的门,然后走了出去。
终于,布万库尔出现了。
“你好啊!”我对他说,“你这是搞了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开始,我完全被他的样子吓住了。然后,我慢慢明白了让我惊讶的原因。这位物理学家看起来像是被一层极其轻薄的雾气包围着—— 一种带着紫色光泽的薄雾,看起来像是霉斑的颜色,包裹住他全身,形成了一层透明的雾膜。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臭氧味。
可布万库尔本人看起来倒是泰然自若。“好了!”他说,语气平静,“看上去确实挺奇怪的。肯定是那该死的实验留下的残留现象。一会儿就会慢慢消散。”
他伸手要跟我握手。包裹着他身体的那层淡紫色光晕虽然摸不着,但他那只手却软得吓人。突然,这位科学家把手从我掌心里抽回去,按住了胸口,明显是因为心悸。
“你现在不舒服,我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休息。要不我给你检查一下?”
“哎哎哎——别像小孩子一样,医生!一会儿就消散了。我跟你保证,一小时内肯定就看不到了。再说了,那实验失败就失败,见鬼去吧,反正你在这里,又回来了!我们换个话题行不行?你觉得这个新装饰怎么样?那个挂饰不错吧?还有那面镜子!圣戈班5的东西,老兄!”
就在这时,我们都猛地愣住了,原地石化。我们疑惑地看着彼此,谁也不敢先开口。最后,布万库尔声音颤抖地问我:“没错吧?你也能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错,”我结结巴巴地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奇迹出现了。我不记得是我们谁先注意到的,可以确定的是,虽然我们两人都站在镜子前面,但镜子里只映出了我的倒影,布万库尔的倒影——消失了!在他本该出现的位置上,只能看到书桌的清晰倒影,和更远处黑板的影子。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布万库尔开始大喊大叫,兴奋不已。过了一会儿,他渐渐平静下来。“哎呀,老兄,”他说,“我看啊,这是个了不起的大发现……一个我没想到的成果。多精彩啊,朋友!什么都没有!太精彩了,亲爱的医生!不过我得承认,我没明白为什么。我想不通原因……”
“你那圈淡紫色光晕……”我提醒他。
“嘘!”布万库尔说,“闭嘴。”
他坐在那面镜子前,镜子里没有他的倒影,他一边大笑着比手画脚,一边开始了一通自说自话的辩论,“你看,医生,我能部分理解是怎么回事。因为某些原因——我不会告诉你,省得你劈头盖脸地骂我——我给自己注射了一种特殊的液体,没想到它的附着力竟然这么强。我估计我现在全身都充满了这种东西,那圈光晕大概就是我体内多余的液体逸散出来的结果。”
“我们最近才发现这种气体——或者说这种光,随你怎么叫吧——有一种出人意料的特性。我原本只以为它能穿透那些紫外线可以通过的材料,比如肉体、木头之类的,再加上骨头和玻璃7。而它现在显现出来的这个出人意料的特质,虽然跟我最初的猜测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解释不了。X射线确实无法被反射,可是……”
“反射的原理现在光学界也还没弄明白吧?”我问。
“没有。关于反射,光学研究的只是一些结果,而这些结果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光学记录下某些现象,然后根据这些现象的重复出现归纳出一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叫作‘定律’,因为至今还没有推翻这些规律的证据。光,也就是所有这些光学现象的主角,本身还是个谜。这个谜之所以如此难解,是因为它的一半现象虽然早已被确认并深入研究多年,却根本无法直接感知。它们不仅像可见光一样无形、无声、无味、无嗅,而且还是冰冷和黑暗的。”
“是啊,就在十年前,人们还以为光只是被物体反射出来的,反射程度有多有少而已,但从来不会真正进入物体内部。”布万库尔提高了声音,“多么神奇!所有的物质,全都被穿透了!”他用弯曲的食指敲了敲自己那张桃花心木的扶手椅。突然,他好像灵机一动,俯身靠近镜子,也用同样的方式敲了敲镜面。
这一敲把我吓得惊呼出声。他的手指轻易地穿透了镜面,就像穿过平静的水面!指尖接触的地方泛起了一圈圈水波似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开来,扰乱了那垂直“镜湖”的清澈平静。
布万库尔浑身一震,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他毅然站起身,朝镜子走去,整个人完全没入镜中,只发出一阵像纸张轻响的沙沙声。镜面上出现了一个旋涡,倒影扭曲旋转。等一切重新归于平静时,我看见那个泛着紫光的人站在了镜子的另一边。他上下看了看我,无声地笑了起来,舒服地坐在那张扶手椅的倒影中。
我伸手一摸,圣戈班出品的镜子依然坚实无比、纹丝不动。
在镜子倒映出来的书房里,布万库尔动着嘴唇,但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把头探出我们之间那道奇异的分界线,镜中的画面再次被打乱。
“多奇怪的地方啊!”他对我说,“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
“我也听不见——不过你能不能换种交流方式?你这样进进出出,我有些时候是看不清楚的。”
“我自己也看不清。我在书房里看你,就像你在倒影里看我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这边陪着我的是你的影子。”
他把头又缩回了那个神秘的世界。他的行动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困难,还不时触摸并感受身边的物体。他从一个架子上挪动了一个烧瓶,那头一响,我转头看现实中的书房,只见那个真正的烧瓶短暂地升了起来,然后又重新落回原位。就这样,布万库尔在镜中的书房做出的动作,在现实中引发了对称的变化。他经过我的镜像的时候,还特地绕着那个我转了一圈。有一次,他故意轻轻推了那个我一下,然后我感到有个看不见的人把我往旁边推了一下。
做了一些这样的实验后,布万库尔站在黑板的镜像前。他好像在右边找什么,忽然一拍脑门,原来海绵在他的左边。他擦掉了黑板上的公式和符号,然后拿起一截粉笔写了起来。他写得特别大,好让我站在镜面这一边也能看清。他时不时离开黑板,到镜中各处探查,验证某些假设,或是测验某些猜想,然后又跑回来写下实验结果。在我身后,那截现实中的粉笔也在真实的黑板上“嗒嗒嗒”地敲着,仿佛是电报机在工作,写出来的是从右到左、潦草难辨的一串反过来的字符。
布万库尔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把它们一字一句抄在了笔记本上,因为那些字写得太大,不一会儿就占满了整块黑板,只能不断擦掉再写。
我身处一片陌生的区域。在这里呼吸毫无困难。它究竟位于何处?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想。眼下,我得仔细观察。
现实世界的所有镜像都软得过分——几乎要散架。我所在的这个房间到我能看到的镜面边界就戛然而止。在我这边,镜子靠的那堵墙变成了一片黑暗,中间有一个发光的矩形……那是一个漆黑的平面,任何物质都无法穿透。看着就让人不安,摸起来更是毛骨悚然。它不粗糙、不坚硬也不温热,就是无法穿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如果我打开窗户,那片浓重的黑夜也会向镜像的风景两侧延伸。这种黑暗也构成了所有镜像中未被反射的部分,比如你自己的镜像的背面,医生。你的镜像有两部分,面向镜子的那半和你一样,背对镜子的那半则完全由那可怖的黑暗组成。两者之间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哪怕你转身,那条线都不会动,就像你晚上站在一堆明亮的篝火前,无论怎么转身,身体始终一半被照亮,一半在阴影中。
氨水没味道。液体没有味道。拉姆斯登机释放出的是假火花,指向莱顿瓶时完全没有能量。8
在我们通过文字交流的时候,我想把自己的疑问告诉布万库尔——倾斜的镜子、天花板的镜子,还有地板上的镜子里出现了什么现象?我还想告诉他自己想要在这些不同的镜子场景中施加重量,甚至就在现在这个场景。为此,我主动擦去了黑板上的字,只花了几秒钟。
我刚开始写我的提议,那截粉笔却突然猛地从我手中飞了出去。它以一种歪歪扭扭、颤抖不稳的字迹,从左到右写出了一串正常的字(说明这回是布万库尔自己特意反着写的,不惜一切地想让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救命!”就在这一瞬,一个模糊的人形出现在我身边,手里正握着那截白色的粉笔。
我冲到镜子前,布万库尔在镜中朝我奔来。他的额头已经鲜血淋漓。他全力撞向镜面,仿佛想要将它砸碎——可那镜面比花岗岩还坚硬。这面镜子已经变得完全无法穿透,变成了某种不可理解的坚固之物,从那个世界带来的所有力量都在此处失效。科学家的头部又添了一道伤口,已经被鲜血染红。我明白过来,在我刚才短暂离开镜子的时候,他已经试图逃出来过一次了。那圈淡紫色的光晕已经消散,而这个可怜的人,被那种液体——毫无疑问是维持他在那个陌生环境中存活的关键物质——抛弃了,现在开始出现明显的窒息迹象。
他一次又一次地冲过来,一次次狠狠撞在那无法被撼动的分隔面上,把自己撞得遍体鳞伤。最可怕的是——我亲眼看到他的影子逐渐在我这边重新显现出来,出现了另一个血淋淋的布万库尔,疯狂、骇人,还有黑色的一半身影。这两个困兽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他们的嘴唇扭动着,发出无声的号叫和求救声,一遍又一遍地扑向对方——手碰手,额头撞额头,血碰血——他们一次次撞在彼此身上,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野蛮动作和同样的无效挣扎。
我试着——是出于什么本能,或什么直觉?——把这个镜像拖进实验室。然而,当那个模糊不定的存在到达镜子的视觉边界时,就被某种最坚不可摧的东西给拦住了,停在了那里。那道界线斜斜地穿过实验室大开的门,对那位科学家的幽影而言,它比任何瓦砾堆成的堡垒还要坚固,将他挡在外面。我拼尽全力拉他,试图把他推过那道我无法感知的无形屏障,却怎么也无法让他穿过去。他与布万库尔的真实身体密不可分,而我竟忘了,那具身体此刻仍被困在那个奇异的空间。
可我不能什么都不做。这个镜像已经在我怀里喘不过气来了。我该怎么办?我让他躺在地上——然后,我看到镜子深处的布万库尔也同时仰躺下来,脸色通红,双眼紧闭。
我下定了决心。客厅壁炉那边有一套十八世纪的大铁火钳,我跑去拿来了其中一件。
第一下砸下去,镜面就从一边到另一边裂开了一道大缝。几下之后,整面镜子很快变成了一堆碎片。我看见了背后的墙,火钳在那堵厚厚的墙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我转过身,布万库尔的镜像已经消失不见了。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管家已经被那声巨响吸引过来了。
“怎么了?什么情况?”我进到客厅,问她。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指着自己倒在木地板上的主人。他一动不动。一张还保持在原位的支架桌的桌腿,穿透了他的腿部。
我要在此郑重声明:就在一分钟前,我还走进客厅去拿火钳,那时房间里绝对空无一人。
这位物理学家还活着。经过几次有节奏地拉动舌头,再加上几轮人工呼吸,他终于恢复了意识——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把那张支架桌弄松,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才把那根木头从他腿上拔了出来。拔出桌腿后,留下的创口异常平滑,干净利落地穿透了肌肉,擦着大腿骨而过。说实话,说是“伤口”都有点勉强,它更像是一个孔,边缘完全没有瘀伤。也就是说,那张桌子的重量并没有砸入大腿。再说了,那根桌腿还是固定死的。甚至可以说——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他那条腿仿佛是在桌腿周围重新长好的,像模具一样包住了桌腿。
不过,我没空细想这些,布万库尔的身体状况需要我全神贯注。真正威胁他生命的并不是那条腿的伤,而是他身上密布的溃疡,以及体内那些诡异的灼伤——这些伤说不定会留下永久性损害。他的症状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严重的皮肤炎,还伴随着大量脱发的症状,手指甲和脚趾甲也出了问题。总之,他表现出了长期暴露在不可见光线下的所有典型症状,在瞬间摄影技术出现之前,我曾在许多接受过X光检查的病人身上多次见过类似情况。
此外,布万库尔向我承认,他曾试图拍摄一盏铁制烛台,要透过他自己的身体和一块玻璃来拍——那次实验中途失败了,就是我在开头所讲的那个实验,也就是这整个奇异事件的开端。“我用镭和铂的混合物制成了电极的金属。”他对我说。他在床上不停地跟我说话,同时还时不时咒骂着那场让他远离实验、无法继续破解谜题的倒霉事故,不过他的咒骂也都无伤大雅。
为了让他冷静下来,我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一一告诉他,也强调我们必须把现有的所有确定信息整理出来,用来构建一个合理的假设,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推进研究。我还特地回到几个关键的位置做实地调查,希望通过勘查,找到更多证据佐证我们的记录。结果我只发现了一件事:那张客厅里的支架桌,和被打碎的镜面在空间上是完全对称的——刚好对应我当时在书房里放下布万库尔镜像的位置。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科学家。
“你知道幻灯机制造者玩的一种手法,叫‘融景’吗?”他问我。
“知道,”我回答,“就是把投影在幕布上的一幅图像,替换成另一幅图像。这个效果是靠两台投影机来实现的。第一幅图像慢慢变暗,同时第二幅图像慢慢显露出来。”
“那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物理学家继续说,“在某一个时刻,两幅图像会同时出现在幕布上,彼此交融、重叠——比如说,一群朋友的合影中突然冒出一艘船的桅杆……”
“所以呢?”我问他,“这跟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
“你想象一下,”科学家打断我,“第一张图是我的肖像,第二张图是那张路易十五风格的支架桌。我觉得这似乎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你砸碎镜子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如果那张桌子正好是在我的客厅里拍摄的,而可怜的朋友你则是在书房里……”
“可这根本没解释清楚。”我说。
“确实。不过话说回来,不管理智怎么认为,我们经历的一切似乎都在支持一种说法——镜子背后或许真藏着一个空间……”
“可你设想的那个……怎么说呢……临时空间到底在哪儿呢?”我反驳道,“就拿这次来说,那面镜子里的书房镜像,位置上正好与客厅重合。”
“对——正是如此。”教授说。
“可说到底,布万库尔,客厅就是客厅啊!同一个空间怎么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东西——这太荒谬了!”
“哼!”他皱着脸,说,“荒谬!首先,确实存在融景。再说了,我们只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可我们根本不了解它们。广袤与永恒,是人类无法想象的。你能说自己详细了解一个整体的某个部分,可你其实并不了解那个整体吗?你确定两件事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时间吗?你敢说它们就一定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
他用戏谑的语气补充道:“毕竟,我的身体所占据的空间,在同一时刻既属于一个病人,也属于一个选民,不排除还有别人的……”
我松了一口气,他显然在开玩笑,我们的话题也就自然换了。毕竟,这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唯有通过实验证明,才能让我们心服口服——虽然有时我也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如我认为自己看到的那样发生过。
布万库尔刚刚恢复,还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就又开始了他的研究。为了防止泄密,他把菲利克斯打发走了——由我尽我所能地接替他的工作——然后我们便开始投入实验。
先说结论吧:所谓临时空间(我们以后就这么叫它,以便和恒定空间区分开)再也没有重新开启。出于谨慎,我们用了几只豚鼠做实验,可它们全都死于各种疾病——有的掉光了毛,有的长满了溃疡,有的没有了爪子,还有几只抽搐不止,死因不明。在经历多次失败后,布万库尔试图人工复现电车火花时,有三只豚鼠当场毙命,还有一只被布万库尔弄死了——当时他怒火中烧,执意要把它强行塞进镜子里。可无一例外,没有一只豚鼠成功进入那个镜中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在它们体内激发出传说中的紫色透明光晕。
我放弃了这个项目。布万库尔却执意要继续。“你错了,”他对我说,“我有个推断。世界上不只有玻璃镜……还有其他材质也具有反射能力,而且更容易穿透……”
可怜的布万库尔!他多么顽固地追逐着自己的幻想啊!那种执着与胆量,真令人敬佩!我已经给他开出了严格的治疗方案,警告他再不遵医嘱就会死。他却完全不当回事,仍旧天天暴露在那些几乎要了他命的可怕辐射之下。每天,我都眼睁睁看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黄,秃顶的脑袋越垂越低。那些病症一个个地冒出来。他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可怖,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过了一阵子,他对我说,在他发现真相的那一天,可能最让他高兴的不是科学上的胜利,而是终于不用再对着镜子冥思苦想了。
“不过,耐心点!”他补充道,“再给我一两周,科学院就要听到些新鲜玩意儿了!”
昨天凌晨,一位运河船夫在牵引道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交到了警察局,一位眼光敏锐的警官认出那些是“化学设备”。他随即赶往布万库尔的住所,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到了以后,他得知那位科学家前一晚就已失踪。
后来,人们从运河里捞出了他的尸体。
“世界上确实有比玻璃更易穿透并同样具备反射能力的物质……”
有人说他是在触电后不慎落水身亡,也有人委婉地补充道:“也许他的管家知道些什么。”
《蓬塔尔吉斯回声报》则坚定地写道:“他是自杀的。因长期从事危险实验,他早已患上了不治之症。”
也曾有人带着讽刺的微笑,对我说:“他的大脑是被冷光灼伤的,哼哼!”
可只有我知道真相。
我仿佛能看到布万库尔站在那条夜色中的运河边。他把电池的锌电极浸进重铬酸液中,很快,鲁姆科夫线圈开始发出蜜蜂般或大黄蜂般的嗡嗡声,灯泡泛起磷光。科学家相信自己此刻已填满了某种神秘的澄清物质。
他看着水的深处,看着那片倒映出来的宁静景色……
然后他缓缓下沉,不知道那个宇宙中是否也有引力,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这样坠入脚下展开的星空之渊。
他下沉着……可他最终只发现了恒定空间——换句话说,就是现实中的水。那是沉重之水,无法供人类生存。那是结局之水,静默得仿佛所有故事最后的沉默。那是终极之水。
1奥布松是法国克勒兹省的一个市镇,曾因其地毯和挂毯而久负盛名,这些挂毯常常描绘狩猎场景,其中许多作品在17世纪时获得了皇家认证。
2位于蒙马特大道10号,创立于1882年,以其首任艺术总监阿尔弗雷德·格雷万的名字命名,是巴黎的蜡像博物馆,相当于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
3即X射线,是一种频率极高、波长极短、能量很大的电磁波。
4系一种早期的放电管,由威廉·克鲁克斯于19世纪70年代发明,其构成为一根部分抽真空的玻璃管,两端各有一个电极。它不同于后来的阴极射线管,因为其电极不加热,不能直接发射电子。克鲁克斯管通常由鲁姆科夫感应线圈驱动,就如布万库尔使用的那样;正是这种装置使伦琴在1895年意外发现了X射线。
5现在是一家跨国公司,最初则是法国政府在17世纪为对抗威尼斯玻璃产业、发展本土玻璃与镜子制造而设立的企业。
6法国著名画家安格尔业余时间以拉小提琴为乐,因此“安格尔的小提琴”在19世纪成为指代“第二爱好”的流行说法。
7紫外线虽具备一定的穿透力,但仍难以穿透肉体和木头等物质。结合后文,大概率是受其时代科技水平所限,作者在“紫外线”和“X射线”两概念上出现了混用。——编者注
8拉姆斯登机是一种利用旋转圆盘通过摩擦产生静电的装置,而莱顿瓶则是一种储存静电的装置,它的结构是在一个瓶子上设置两个电极,一个位于瓶内,一个位于瓶外。
(《科幻世界》2025年7期[58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