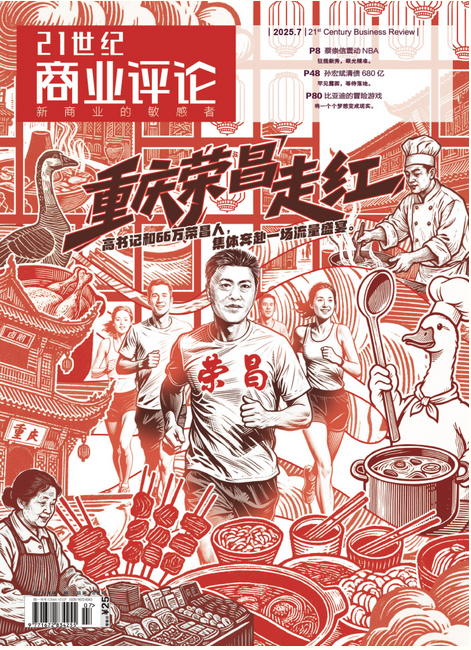
当比亚迪在电池做到领先时,王传福开始思考更远的未来。
2002年7月,比亚迪在H股上市时,招股书提出,约9000万元供动力电池的研究、开发及制造,计划设立试生产线,于2004年逐步开始产业化生产。
“消费类电池只是个百亿产业,不够大,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比亚迪要进入更大的产业领域,又希望和电池相关。”
在香港上市融资后,业务可选项很多,王传福做战略决策时,首先分析的是技术。他始终认为,对技术的前瞻性判断能让企业走上更广阔、更长远的航道。
企业家的雄心,会驱动企业驶向无限可能的新天地。比亚迪只讲到要投资动力电池,没过多久,王传福就驶出预定的轨道。
2003年,他决定进军汽车产业,当时这是一个充满反对声的“冒险者游戏”。
攻关纯电
一开始,王传福看到汽车产业的机会,他想做电动汽车。
作为电池制造的代表,比亚迪从1996年就研究大容量镍电池,其可适用于电动汽车,王传福由此萌生了强烈的汽车梦。
1997年5月的一天,在天津电报大楼,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张国庆,和王传福通电话,专门讨论如何做电动汽车电池,当年7月,他就加入比亚迪被委以重任,担任汽车电池组组长和镍氢电池组组长。
比亚迪中央研究部很快建成研发队伍,由200多名教授、博士生、硕士生等专家组成,配备有XPS(X射线光电子能谱技术)、ICP(电感耦合系离子体技术)等先进技术和仪器设备,致力于新能源研究。
为了做电池实验,比亚迪计划进口电动汽车。
王传福去北京试驾了一辆红色的北京牌汽车,型号为BJ6490D,车身印有“电动小客车”字样。王传福花15万元购买了那辆车。车到比亚迪后,张国庆等工程师跟着司机练车,测试续驶里程、动力性能等数据。后来,比亚迪用自己的镍电池替换了原车的铅酸电池。
比亚迪的工作引起了重视。
1999年,广东省将电动汽车电池的研制,作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下达给比亚迪,要求它提供可装车的高性能镍动力电池,适配车辆即为粤海EV6460N。
据相关验收记录,EV6460N的技术指标为,速度110公里/小时,续航里程130公里,0~40公里/小时的加速时间为8.5秒,“基本达到国外同类型电动汽车的技术水平。”
对攻克动力电池技术,王传福很有信心。有人问:“通用汽车都放弃了EV1,电动汽车还有前景吗?”他回答:“通用放弃了,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锂电池发展这么快。我相信未来的电动汽车电池就是锂电池。”
2002年10月,比亚迪启动开发车用锂离子电池的课题。课题组要做设计、做实验,还要和设备团队沟通,考虑结构设计的实现问题。
按王传福的要求,研发人员先以200~300公里的续驶里程为目标,把电池的基本框架确定下来,再从结构、电化学材料等方向分头研究。
后为比亚迪电池业务带头人的何龙,那时还没有加入课题组,课题组的一些做法让他印象深刻。
“他们用100瓦的白炽灯做放电测试,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装了很多个灯泡。你难以想象,就这么几个人,要用土办法研究世界难题。”课题组每天都在“折腾”。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用的方法对不对,就是敢于尝试,也乐在其中。
为了形成高压,他们把很多电池连在一起,一旦短路,车上的钢板就会被瞬间击穿。在实验过程中,发生过很多次小爆炸。他们会分析每次爆炸的原因,研究电池如何防护,电池和车之间怎么绝缘,再调整,直到产品过关。
当时,日本丰田纯电动汽车采用镍氢电池,一次充电行驶距离为160公里。比亚迪攻关纯电汽车,一开始就采用了锂离子电池,一次充电可行驶250公里以上。
2002年,王传福买的那辆电动小客车仍在使用。
比亚迪的研发人员给它装上了锂离子电池,在庞大的厂区内试车。最初的红色车身被涂成了绿色,当初的车牌BJ6490D也换成“锂电动力汽车BYD-001(试)”的字样,进气格栅则写着大大的“BYD”。
入主秦川
“万花明曲水,车马动秦川。”
当王传福带着动力电池技术以及电池、电子产业的制造能力,准备叩响汽车产业之门时,他没有想到,这扇门是遥远的古城西安为他打开的。
2002年下半年,王传福出差的次数变多了,尤其是到北京。一到周末,他就走访汽车模具厂、汽车设计院、汽车发动机厂等,和专业人士交流,有时一聊就到半夜。王传福每次到北京,也必去新华书店买与汽车相关的书。
他还到过西安、潍坊和山西等地,调研工厂、汽车变速箱、齿轮制造等情况。“我一开始觉得造车很难,后来发现也没那么神秘。汽车行业比较传统,它有成套的设备供应商,有专门的设计院......只做拼装的话,非常简单。”
王传福也清醒地看到,电动汽车的技术、市场尚不成熟,要生存下去,就得“两条腿走路”:其一,要着手电动汽车的开发,掌握核心技术;其二,得做燃油车,作为过渡,借此摸清汽车产业链的情况,积累能力。
2002年10月7日,王传福认识了时任秦川机械厂的厂长李永钊,他得知王传福有意造车,便介绍给他由秦川机械厂、陕投集团共同持股的秦川汽车,并邀请他到西安考察。
10天后,王传福带着财务总监吴经胜、采购负责人方芳一行三人来到西安,李永钊带着他们到秦川汽车进行现场考察,并见到时任秦川汽车董事长的杨有庄。
在聊起收购事宜时,杨有庄觉得非常突然,秦川汽车那几年与奔驰、菲亚特等国际企业谈过合作,也与国内的华晨、海马等车企有过深入接触,他没有想过业内名不见经传的比亚迪会来谈收购。
杨不知如何应答,只是笑着说:“小年轻,我干了很长时间汽车了,干汽车要有新技术,要有大投入,不好干啊。”王传福说:“干汽车,我能干到 80岁,给我几十年,一定能干出名堂!要是干不好,是我真没本事。”
第二天,王传福去拜会秦川汽车的大股东——陕投集团的时任董事长冯煦初。冯起初说:“秦川汽车要找一个有实力、有基础、有条件的‘婆家’。”
第三天,两人再次见面,双方聊了一小时,冯煦初答应等比亚迪考察后尽快向省政府汇报。
没过多久,王传福又多次赴西安了解情况。在秦川汽车的工厂里,他绕来绕去,看得仔仔细细。
时任秦川汽车总经理的刘振宇接待过很多来谈收购的人,“假的、真的、二道贩子,什么都有”,结果发现,没有造车经历的王传福来工厂的次数最多,最爱问汽车本身的问题。
刘见其诚恳,便和他交了心,也交了底:秦川汽车有些债务,但没有呆坏账;拥有年产5万辆轿车的综合生产能力,2000年底完成“四大工艺”生产线建设;有近千名员工,含近百名中级或以上的工程师及技术员,很多人参与过“福莱尔”的开发。
福莱尔是秦川汽车自己设计的,没有用别人的车型,王传福对不受制于人的做法非常认同。
2003年1月,比亚迪分别与陕投集团和秦川机械厂签订收购协议,组建比亚迪汽车,签约后,立即依约支付2.695亿元投资款。从双方接触到完成收购,只用了三个月。
收购公告发出后,投资者在第一时间把比亚迪的电话打爆了。“比亚迪造手机电池行,造电动车是忽悠。”甚至有基金经理放出狠话:“如果比亚迪坚持收购,我们就抛售股票,直到抛死为止!”
短短两天,比亚迪市值蒸发近27亿港元,王传福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但毫不退缩,他说:“我下半辈子就干汽车了!”
出师未捷
“门外汉”比亚迪入主秦川汽车后,显得很有章法。
王传福将开发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加大人才的引进、选拔和培养,且引进六西格玛管理和QS9000系列管理体系,全力改造秦川汽车。
时任IC(集成电路)团队经理的罗如忠回忆,2003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比亚迪深圳葵涌办公楼,王传福召集IC团队开会,说:“你们开始了解变速箱吧。”他希望,IC团队通过对变速箱的了解,结合微电子技术,将福莱尔的手动变速箱替代成自动变速箱。
很快,比亚迪买了一辆搭载AMT(机械式自动变速器)的奔驰车,放在办公楼前,供大家拆解学习。
大家动了没几下,就停下来——由于没有摸清楚特殊的安装构造,对零部件只能硬拆,如果这样做,一辆崭新的汽车就再也不能复原了,大家舍不得拆。
眼见大家愣着,王传福拿起一把钥匙,在车身上用力划了几道说:“这下你们就敢拆了!拆下来做研究,反复拆几次不就会了吗?”
他还说,就算一辆车价值100万元,只要在拆的过程中能学会一项技术,这100万元就赚回来了。
收购秦川汽车第四天,比亚迪与上海同济同捷科技签订合同。双方商定,在福莱尔轿车基础上设计4款车,代号分别为216、316、416、516,对应车型为加宽两厢轿车、三厢轿车、小型MPV和小型SUV(运动型多功能汽车)。
确定收购秦川汽车的意向之后,王传福就将产品规划提上议事日程,他先将汽车研发中心放在上海,那里是中国汽车重镇,周边的产业链配套齐全,人才众多。
廉玉波是同济同捷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02年,王传福在寻找整车设计的合作伙伴时,与他相识,并把他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两年后,40岁的廉玉波加入比亚迪。
经过约一年的设计开发,2004年1月,“316”终于成型。这是一辆4.2米长、1.6L(升)排气量的家用小排量轿车。车身在福莱尔车的基础上加宽,再在后面加一个后备箱。发动机是三菱的,底盘系统则是哈飞赛马和捷达的融合。
那年的2月29日,上海的气温不到3℃,阴雨蒙蒙,寒风刺骨。
经销商们围着样车,仔细地看了又看,起初都没出声,好一会儿才有人说:“这款车太丑了!”比亚迪给他们发了一张调查问卷,结果无论外观、内饰还是动力,都被他们画上了“×”。
现场所有造车人的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7个经销商走了6个。
这是比亚迪第一次造车,对汽车的很多规律和个中奥妙都不懂,造型评审时觉得没问题,等车做出来,才发现比较丑。怎么办?如果不生产这个车型,再推出一款新车,可能又要花费几亿元的模具费用以及至少一两年的时间。
王传福清楚,一个没有特点的产品进入市场后,如果卖不好,将造成更大损失。“好比你一开始投了2个亿,现在砍掉,损失2个亿;不砍掉,继续产,继续卖,造成经销商积压,可能损失3个亿;加上对品牌的损害,可能是4个亿。”
出师未捷,王传福一宿无眠,他花了一个晚上思考:继续做?停掉?重新开发?第二天早上,他做出了决定:砍掉“316”!
第二天白天,他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包括负责供应链的经理。廉玉波被约到王的办公室时,已是半夜。“我们要赶紧策划一款新车,一年时间就要做出来。”“时间太短了,这在汽车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以前没做过,没经验,人也很少。”廉说。
王传福斩钉截铁回答:“我们就是要干汽车历史上不可能的事。”于是,“神车”F3开始萌芽。
垂直整合
“316”的教训,让比亚迪人真正思考怎样造车: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理解和选择是怎样的?如何打造一款让市场接受、价格合适的车?车型该怎样定位?他们进行大量市场调研,也去欧美考察。
廉玉波则用一周时间全方位思考,然后给了王传福一个答案:做一款家用轿车。
当时,桑塔纳和捷达在中国很流行,奇瑞推出的家用轿车“旗云”也卖得不错。这些车型针对的人群广泛,老少皆宜,车型大小适中,不管是家用还是商用都合适,价格在10万元以内,符合大众消费水平。
廉玉波建议就做这一类的车,并提出了可对标车型——丰田卡罗拉。这款车后在中国叫“花冠”,全球一年能卖出100多万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开售。
公司当即买了两辆花冠,并对工程师团队提出要求:第一,把买来的花冠全部拆了,再组装还原,一边拆一边学;第二,新车型不能有专利侵权。
这是典型的逆向研发的做法。将大量的非专利技术任务分派给不同的小组攻关;极少数绕不过去的专利,比如外观专利,就创造性地去改。
“316”下马,王传福没有指责研发团队,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他的宽容与信任让研发团队感到温暖,自信心也得到了保护。在廉玉波的建议下,比亚迪对已规划的车型全部重新梳理,确立了以F3为最优先发展车型的开发计划。
2004年4月,F3项目正式立项,这是面对巨大压力的背水一战。F3能否成功,直接影响着比亚迪汽车未来的命运。
F3的定位已经确定,具体怎么开发和制造还有很多道坎儿。由于 “316”失利,之前的伙伴不愿意再次合作,其他的零部件开发商要么不答应合作,要么报出一个天价。
外援不得,唯有自求。
比亚迪已有自己做零部件、垂直整合的经验,触类旁通,王传福对汽车产业的垂直整合也很有信心。他决定打破整车厂只做四大工艺的常规,增加发动机、变速器、内饰、底盘和汽车电子等零部件产业。比亚迪汽车开启了自主化的垂直整合之路。
上海松江基地的一块场地上,摆满了从车上拆下来的零部件,天窗、升降器、车架、座椅、空调、仪表……什么都有。
只见零部件制造的组长们,一个接一个空手入场,每人抱一个零部件出来。谁拿走了什么,就负责把什么做出来。供应链问题,瞬间全被领走了。
这些组长及他们手下的团队,大多是从电池厂、电子厂划过来的,也没干过汽车。有人懂些机械,有人懂些工程,凡和汽车沾边的,都划过来造车了。比如,以前做结构件注塑的,就把前后保险杠领走了。
王传福买过一本博世的汽车工程手册,里面对零部件讲得很清楚,他给管理者每个人发了一本学习。
现任集团高级副总裁的罗红斌,抢走了仪表和空调。他曾在沈阳电力工程技术研究所工作,2003年加入比亚迪做汽车。在他带领下,F3的仪表、空调都选择业内先进的技术。以空调为例,业内大多采用活塞式压缩机,他们一开始就选择更高水平的涡旋压缩机,做出了制冷效果好、能效高的产品。
除了压缩机,空调的管路、蒸发器、冷凝器等零部件,也都自己做,成本可控,垂直整合的优势尽显。
一炮而红
2004年7月31日,比亚迪成立汽车产业群。当天,业务工作会在比亚迪上海分公司召开,会上决定先后成立5个生产型事业部、2个研发部门、1个检测中心和相关职能部门。
当晚,王传福宴请汽车产业群的各位经理,他们激动地合唱了《真心英雄》和《同一首歌》。
比亚迪从其IT产业群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给每个汽车事业部配备了带头人,确定研发方向和工作目标。廉玉波被任命为汽车产业群总工程师。
F3项目里有机械专业的人才,也有材料、电子等专业的人才,这支年轻的“混成旅”,每天连轴转,先把车拼出来,再对一个个技术细节进行攻坚。汽车零部件太多了,分解到下一层则更多,经常是一个问题牵出更多问题。团队白天干活,晚上10点开会总结,十一二点结束,第二天继续如此,周而复始。
最初,比亚迪只针对部分零部件自行开发设计,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自主开发零部件大大缩短开发周期。由于内部沟通交流十分畅通,一张设计图纸刚出炉,就会传到生产部门进行开发生产。生产过程中发现不足,也能及时更改设计。
按照惯例,一个新车型开发周期至少三年,F3从立项到车型下线仅用12个月。
“时间紧,任务重,技术能力有限,但我们把所有压力转化成了无尽的动力。每次遇到困难,看到王总坚毅的眼神,我们没有退缩的理由。”F3项目经理段伟回忆说,团队也和王总发过小脾气,得益他的宽容,沟通都是无障碍的。
2005年4月,比亚迪汽车F3新车下线暨新厂落成庆典,在西安比亚迪高新区新型工业园举行。F3拥有5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是比亚迪自主打造的第一款正式亮相的汽车。王传福在庆典上激昂致辞,“一定会打拼出中国民族汽车的新天地!”
同年6月初,F3在天津汽车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一“撞”惊人。检测数据表明:F3的乘员头部危险指数为231,国家危险值标准指数为1000。专家分析认为,该车的安全系数高于国家标准,已达国际水准。
F3在西安成功下线时,被邀请到现场看车的经销商,都点头看好,看着展出的5辆车,感觉和看“316”时完全不一样。新车亮相让人振奋。比亚迪的生产能力、营销力量有限,无法像别的品牌搞全国同步上市。
F3从下线到设计销售方案,耗时5个多月,直至“分时分站”销售方案出现时才被通过。
其策略颇有点“田忌赛马”的味道:首先在某个中等城市试水,选择对手力量薄弱但又具有消费潜力,且在比亚迪生产基地半径辐射范围内、物流成本可控的地方。这样,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五指成拳,只打一个点。
当年9月22日,山东济南成为F3上市的第一站,之所以选择济南,基于四点理由:第一,山东没有大牌主机厂,竞争没那么激烈;第二,山东人口众多,经济向好,有消费潜力;第三,山东的高速道路设施完善,道路通畅,利于车辆物流运输、市场辐射;第四,比亚迪在山东的销售网络,能够承担营销推广的任务。
捷报传来,F3在济南上市当天,销售量加上订单量超过2000辆。
F3一上市就成为车市中的重磅炸弹,掀起一波又一波抢购热潮。随着F3在全国各地铺货,2006年一季度,F3夺得“三冠王”:全国产量增幅冠军、销量增幅冠军、国内单一车型中级家庭轿车的销量冠军。
到2007年,F3单月销量突破10000辆,中国品牌以单一车型首次跨入“万辆俱乐部”。
乘势而上
2006年5月,F3基本完成全国上市,再到2007年6月第10万辆车下线,比亚迪用了14个月的时间。
F3是比亚迪进入汽车产业的里程碑和新起点,标志着其汽车产业布局和体系的正式建立,并进入高效、有序运转的阶段。
F3一战成名,比亚迪乘势而上。2006年2月,在比亚迪车型模具任务三年规划会议上,公司系统梳理了未来燃油车型的方向,规划了F1、F3-HRV、F6、M3、M6、S6等多款车型,基本上形成以轿车、MPV、SUV三大系列,3、6、9三个档次的“三纵三横”的整体规划方案。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比亚迪已有的产业布局和生产基地显得捉襟见肘。早在2003年8月,比亚迪便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陕投集团签约,在高新区征地1500亩,建设轿车、电动汽车研发和生产基地,项目投资20亿元,年产汽车20万辆,新厂在2005年4月落成。
那时,比亚迪汽车研发在上海,生产在西安,销售和决策在深圳,沟通效率受到一定影响,王传福决定,打造一个集研发、生产、决策中心、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基地。深圳作为比亚迪的发源地,成为新基地的不二之选。
2006年,比亚迪开始筹备深圳基地的建设,并着手整体规划深圳汽车项目。
当年9月,深圳坪山基地开始建设,仅仅11个月、329天里,比亚迪削平30多座山头,填平120多个鱼塘,挖出750万立方米土石方,建成各类建筑物112万平方米,建设自有发电厂和16栋生产厂房。
同时,比亚迪也引进了上百台(套)世界领先的整车制造和检测设备。至此,深圳基地也基本具备年产10万辆整车的能力。“比亚迪速度就是这么快,一天可以挖掉一座山。”负责工程建设的王传方说。
2007年8月9日,比亚迪深圳坪山基地落成,比亚迪首款中高级轿车F6同日下线。当天的庆祝仪式上,王传福在致辞中总结了成绩,并对接下来的发展做了目标规划:
“今天,我们将宣布比亚迪新的汽车产业的目标: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在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
王传福要做世界第一的“狂言”,迅速被传播开来。
他很少和媒体打交道,没有受过任何公关训练,他的语言质朴,同时力量强大,包含着自己实践出来的逻辑,而且他真就是这么想的。
同行摇头不信,很多媒体也讽刺嘲笑,他自己非常肯定,中国的市场资源、人才资源,以及勤劳的精神,将助力比亚迪超越哪怕再强大的对手,这已经在电池产业、IT产业得到了印证。
他更坚信,电动车是属于中国的机遇,“比亚迪自己能搞定全部的电动车技术,不会受制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