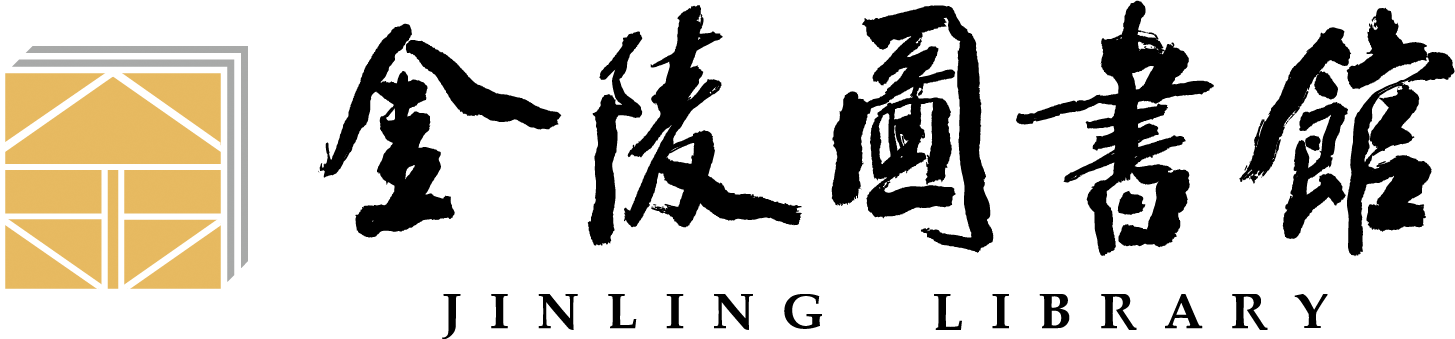![期刊架位号[5760] 期刊架位号[5760]](./W020211221549486764584.png)
濮 颖
每年冬至,我都会想起曾经像鸟雀一样栖息过的小村庄。
苏北平原的村庄大体都是一样的。 一律的灰墙灰瓦,一样的茅舍篱笆,就连喇叭花都开着差不多的颜色,浅紫、粉蓝,缠绕着参差不齐的灌木丛,于是那一片有些晦暗的阴影里就有了几多动人的色彩。 村里的树木很多,除了绿色还是绿色,只有洋槐,一到春天就开出一串串白色的花,花开到花谢的日子里,村庄是甜蜜的。
我爷爷的祖屋在全村最东首的最高处,站在门前,可以看到好多人家低矮的屋檐。 我最喜欢看雨后的那片白色零散地落在有些苍凉的灰瓦上。 屋檐下滴着雨水,低矮的灰云倒映在河塘里,小小年纪竟也会莫名地生出一些伤感,或是叫作惆怅的情绪来。
一年四季,阳光都是先从爷爷家门前经过。 斑驳的光影在移动着,跳跃着。 鸡舍与猪圈也随之亮堂起来。 最东边的那块泥土墙是最先照射到阳光的,也最温热,听奶奶说,幼年的我长期腹泻,看过多少医生不见好,后来是一位老中医开了几服药,其中的药引就是刮下终年第一块被阳光润泽的土屑,用贴身的小衣服包起来,放在我的小肚脐上,竟也治好了我的小儿腹泻。 直到现在,我的印象里总有那一个四围寂静的村庄,东首的高墩上一座农舍,阳光下那一爿黄泥土屋,还有早晨的阳光。
我喜欢在阳光下奔跑,以至于拥有了小麦一样的肤色,还有几点褐色的雀斑。 尽管有人说过,这些斑点就像一泓清澈的水面上零星飘散的几片浮萍,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不同的景致。 我还是会用遮瑕膏去掩盖,就像如今的村庄,总要用水泥混凝土将呼吸着自由空气的黑土地涂抹起来一样,生硬冰冷却总以为是一种很现代的时髦。
我在《童年记事》里写过门前的野枣树。 其实何止是爷爷的门前,几乎各家的门前都有。 听说这些年很多树木都砍了。 这些曾经茂盛的树木都因为村庄的凋敝不再枝繁叶茂,所以被当作了生火的材料。 我只觉可惜。 奶奶说,人是屋的胆,树是人的魂。 人走了,屋破了,树自然就要砍了。 但是我终于还是见到村西的那株高大的桂花树了。 在我心里,这是一株最具浪漫色彩的树。 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我五岁的弟弟在这棵高大的桂花树下给一群猴孩子讲《杨家将》与《岳飞传》,像模像样。 我爷爷则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眯着眼睛,长大嘴巴。 满脸含笑,远远地看着他的孙儿。 我则喜欢爷爷给我讲《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故事。 后来,只要有圆月的晚上,我总会躲在门前老槐树的枝丫缝里看月亮。 月亮里的黑影是吴刚要砍的桂花树。 月亮边上的云朵是嫦娥舒展的衣袖。 零散的星星是嫦娥飞天时散落的佩环。
桂英是在桂花开的时候嫁到江南的。 后来村里的姐妹们都被她带了出去。 她们嫁到了城市的最底层,蜗居在都市繁华的某一个角落。 她们没有没有固定的工作,婆家的兄弟姐妹众多,家庭关系复杂。 从村里人的口气里我听出了隐约的担心和不舍。 直到后来也才觉得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那些从村庄里走进大城市的姑娘们都在异乡站稳了脚跟,生养了儿女。 他们的儿女已经彻底与这个村庄切割,成了地地道道的,操着一口纯粹、流利江南方言的城市人。 这座村庄留给他们的,除了原始、落后与贫穷,就是母亲电话的那一头夹杂的土气的乡音。 我想,这就是她们离开村庄的理由。
村庄确实是小了很多。 河流,树木,房屋,道路,桥梁,还有炊烟。 在我的记忆里,村庄是热闹的。 村民、五谷与六畜滋养了村庄的灵魂,村庄因此才有了匀畅的呼吸与跳动的脉搏。 每当夕阳西下,家家户户烟囱里的炊烟掺和着青草的气息就会飘散开来。 这幅图画一般的场景总是让童年的我从心头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也让幼小的我深深感受到烟火与人家才是最妥的贴合。 这种情结一直滋养着我,直到现在,我依旧执着于“不生烟火何谓人家”的信念。 而这场景总能让我想起小年夜的“送灶”。 我觉得这大约是村庄所有祭祀活动里最贴近生活的一种,以至于我至今还记得这个仪式的过程,包括“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祝祷。 可是当村庄不再有炊烟、灶台的时候,村民们心中的灶王爷又会落在什么地方? 就像村庄周围的蔬菜瓜果大棚,不需要见到阳光雨露,也不需要经历四季的轮回? 工业化生产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片,将漫长复杂的过程切割,也切断了我们的思想和村庄的灵魂。 我总是贪恋自然生长的菜蔬,就像当年村庄的菜园,除了一圈篱笆,没有任何的遮盖,跟我的村庄一样,经历风霜雨露,四季更迭。 月白风清的夜晚,满垄的菜蔬和古老的村庄一起在月光下休眠。 农人不知道什么是岁月静好,只知道晓梦香甜。
最近一次回村庄还是今年的清明节,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 车子开过村西头的那座石板桥便停在一处相对空旷的地方。 村里早没有了年轻人,大多人家都搬去了新庄台上,留下几处破壁残垣和一群不想离开抑或无法离开的老人。 唯有过年时,破旧的门栊上悬贴的鲜红的门笺才显出一点生机,但到底还是破落荒凉得不见烟火。 听人说,祖父母的坟要迁了,跟所有的坟一样要迁移到几里外的公墓去。 随着一起迁移的还有这座村庄的活人,他们要搬到新庄台去,过一种全新的、城市化的生活,眼前的这座村庄很快就要消失了。 如果说,让我们依旧感觉村庄存在的,就是炊烟与坟墓。 炊烟是村庄的入口,坟墓则是村庄最后的坚守。 如今的村庄已然没有了炊烟,可终究还有那片矗立的坟墓存在,它们在风霜雨雪中寂寞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那是留给后人的另一个回归的入口,以至于不让后人忘却。 可如今,这最后的入口也将不复存在,我们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忘记这里,忘记我们不该、不敢、不能忘却的记忆。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