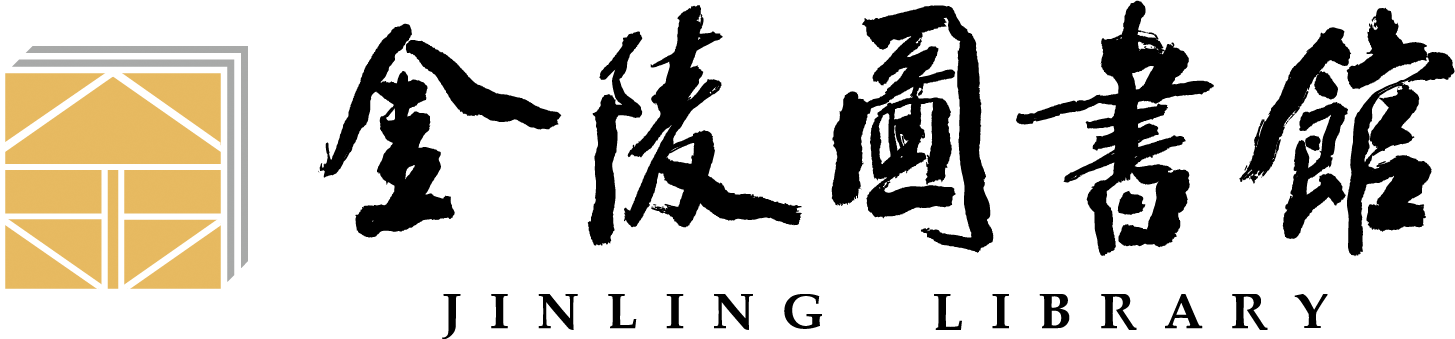一
他拿过的第一数不胜数,尤其是高考。其实,从考场上下来,他心虚得很,语数外物化生,几乎每一科都有几个题目拿不准,但一对答案,竟然都对了。后来的许多个瞬间,他都对此感到恍惚,甚至偶尔会觉得是自己盗取了别人的成绩。
那年夏天,林东镇周围十几个村子流传着他的传说:肖宏力超常发挥,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他如同一匹黑马,不但黑马黑成为校状元,还是市状元。镇高中建校六十年,只出过这么一个市状元。他的照片在学校橱窗里挂了十年,直到后来又出了个自治区状元,才被换下。
出成绩第二天,旗教育局的副局长跟着锣鼓队一起到村里报喜,他父亲光烟就撒了六七条,糖果瓜子无数。那是他们村、他们家、他父亲最为荣耀的一日。
根据村里的习俗,子弟高中是要大张旗鼓祭祖的,何况中的是状元。锣鼓队不用家里请,乡长大手一挥:“就用乡里的。”乡里的锣鼓队平时散在各处,种田的种田,放羊的放羊,过年节或有大型活动时,一声招呼再聚拢起来。最近正在聚集,因为修水库搞大会战,要把大坝加高五米,宣传队不能少。那一年的春晚,当他们看到小品演员宋丹丹和赵本山在电视上摆着手势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一天的场景。
祭祖时,全村人都出动了,邻村和镇上的人也来了不少,整个队伍绵延近一里地,从后山山顶看过去,像一条蠕动的黑虫子。他是虫子的脑袋,白衬衫、青裤子,胸戴大红花。后面紧跟着父亲和乡干部,教育局的领导为了避嫌坐在小车里。
第一站便是到村里的庙宇。
那庙宇自有这个村子时便有,也没人说得清具体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一般寺院正殿的二十分之一大小,形制简单:一间房、一扇门、两扇窗。里面摆着小香案,上立香炉,香炉里插着线香。门两边一副对联:从此去来世,到那莫回头。老人说庙宇虽小,却是人间通往冥界的入口。有人故去,入土前一日,亲朋好友须到此处来给他送行。人们在执事的安排下,焚烧纸钱,洒扫,摆上祭品,哭得井井有条。那时候,逝者肉身已冷,无法再直接听到家人的话,但他们的魂魄仍飘荡在空中。因了庙宇,魂魄可暂时附在神龛上,借助神龛之眼耳,最后一次见亲人,最后一次听他们的叮嘱和不舍。它如同城市里的机场和站台,往生人由此和这一生告别,从阳间去往阴间。
祭祖队伍走到庙宇时,人们已疲累。农历七月的北方正值伏天,太阳辣,紫外线充足,地气蒸腾如热锅。许多人把手摆在头顶处,仿佛能挡住无所不在的阳光,其实只挡住了眼睛上方的一小片。看不见,就当太阳不存在了。
他已从最初的茫然、惊喜和慌乱中平静,并且,自得知那高得超乎想象的分数到此刻已有两日,人们崇拜、惊讶的眼神和一声又一声的赞扬,让他不再觉得那些蒙对的题目是运气。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并非直接来自他的脑细胞。但它总得有个来处,这来处又必然跟他直接相关,否则为何偏偏是他呢?一切绝非偶然,冥冥之中一定有个什么在决定着这世界的运行。
跪下来,他的目光刚好掠过庙宇脊线,远处山峦也如线,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庙宇并不比他高,但那些装饰,和焚烧过的纸钱、香烛之类的烟熏火燎浸染的暗色,却令它十分肃穆。它后面是原野,原野后面是群山,群山后面是整个天空。
许多年前,他作为长孙,曾在这里送别祖父祖母。他们相隔一年去世。每一回,他都跪在一层厚厚的纸钱灰烬上,余温让膝盖微微发痒,继而麻木,可是他一动也不敢动。旁边那个花白长发的女人,他的伯娘,口中念念有词,正在代替家人向祖父祖母交代:“大爷大娘哎,你们放心走呀!啥都不用惦记,什么都给你们准备好啦,到了那边,有钱花有饭吃。你们吃好喝好,保佑孝子贤孙们当官发财呀。”一沓又一沓纸钱点燃,和纸扎的牛马、板车一起被火焰送去那个世界。
他心想,原来死不可怕呀,甚至还有了保佑子孙的法力。
伯娘说:“宏力,跟爷爷说说话,跟奶奶说说话,再不说他们就听不到了。”
他不知说什么,只能轻轻喊一句“爷爷”或者“奶奶”。
“瞅见脚印了没?”伯娘问。
他定睛看,纸灰上什么也没有,扭头见父母和所有亲戚都盯着他,眼巴巴等他的回答。一只蚂蚱从旁边跳到纸灰上,鸣叫着挪动,弹起些许灰尘,极少的一点进入他的鼻孔,他猛地打了个喷嚏。
蚂蚱被吓,极速跃起,竟直接跳进了庙宇的门里。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应该看见,也必须看见,于是他点了点头,说:“看见了。”
伯娘满意地微笑:“行啦,他们带着东西走啦,走得很放心。”
人们开始哭起来,哭声让周围的庄稼都垂下头,整个田野都陷入悲伤的风中。只有他还在想,蚂蚱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出来?
但是今天的祭拜,毫无悲伤之意。
旁边的稻谷已近一米高,等到中秋,最高的那些会比庙宇还高,在风中摇着身躯,等着磨快的镰刀。这一次,没有伯娘,她也在三年前走进庙门,告别人世。
父亲跪在旁边,高声喊:“麻烦那边值事的两间人,去给通报一声啊,我们带着孩子叩谢祖宗来了。感谢爹妈、爷爷奶奶、祖爷爷祖奶奶,感谢列祖列宗,咱们家出状元啦!”
两间人就盘桓于庙宇之上,连通阳间阴间,托梦或传话,于是称两间人。
锣鼓、鞭炮,把正在饱满的庄稼粒都震落了几颗,鸟雀早就被惊到山坡上去了。
接下来,他们要步行几百米,到山坳处的肖家坟地,向爷爷奶奶和诸位祖先叩拜,感谢他们的保佑。
到坟前的时候,围观的人已渐少,那条虫稀稀落落断成了几截。
他按照指示,点燃一堆纸钱。突然,一阵风从山谷吹来,将纸钱燃烧后的灰烬卷到空中,却不吹散,反而形成一股小小的龙卷风,在坟堆上面旋转着。
“哎呀,这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呀!”不知谁喊了一嗓子。
他浑身一激灵,忽然间一切都通了,天地为之宽阔。他仿佛看到了宇宙大爆炸之前的那个奇点,还不及细想,脑袋已被父亲摁到了地上。
“快给祖宗磕头,谢谢他们保佑。”
他哐哐哐磕头,又重又响,却不感到疼。
等直起身,那股龙卷风唰地一下散开,烟灰飞向更高处,打着旋儿消失在青天上,仿佛是谁一把抓住它们,带去了隔壁的世界。
在载着教育局副局长的桑塔纳回村的路上,他心里认定,自己之所以考得这么好,只能是靠祖先保佑。也是从这一刻起,这座小小庙宇,这片坟地,成了他心里最坚实的力量源泉。此后,他再做任何决定时,都有着一股强大的自信。
二
这自信保着他一帆风顺。
本科毕业,读研,进入银行工作,五年后下海创业,他每一步都踩在点上,每个点都踩响了,还一次又一次逢凶化吉。那一回危机,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把全部身家赌博似的投进去,最终逆风翻盘,打了一场漂亮的绝地反击。庆功会上,有人问他是不是有绝密的内幕消息。他微微一笑,说:“祖宗保佑。”旁人以为是句托词,只有他自己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每年的那一天,不管多忙,他都必定回趟老家,载着满车的冥币,独自重走从庙宇到坟地的流程。每一回,他都盯着上旋的青烟怔怔地看好久,既感念冥冥中保佑他的神秘力量,又感到些许不可思议。不过,他只要起身,进入车里,手握方向盘,那种绝对掌握命运的感觉便再次布满全身,像充足了电的机器。时光流逝,眼看着庙宇变得破旧,他出钱整修。时光继续流逝,它再次被岁月和烟火磨损。庙宇周围的庄稼,有时是稻谷,有时是玉米,有时是大豆,高高矮矮,枯枯荣荣,春种秋收。这些年里,他跪在庙宇前,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另一个世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还听见他们的应答声:“好啊,好,好。”
父母去世时,他也是跪在这里把他们送走。他并没有很悲伤,因为此前的经历让他笃信,死去的人并未彻底消失,而是到了新世界,开始了新生活。父母将在那里和他们的父母团聚,保佑他顺遂的人又多了两位。而且,他们过得必然很好,否则怎么会有能力保佑阳间的人呢?
直到疫情来临,他被隔离在小区里。就算不隔离,一路关卡,他也很难回到老家。他第一次没能在那天跪在庙宇前。第二年也是。果然,公司业绩持续下滑,家庭婚姻处处撞车,霉运连连,已近绝境。第三年,他提前半年就开始筹划回乡之旅,为此,一次外差也没出,以保证自己的健康码是绿色的。他备好一切,提前一周就往回走。
他开着车,一路小心翼翼,载着攒了两年的纸钱回到村里,愕然发现庙宇不见了。庄稼地中间,庙宇原来的位置,只剩一片新栽的小树在烈日下摇动,枝叶蔫头耷脑。
他蒙了好一会儿,心抽搐了几下,转而松弛了。不怕走霉运,就怕不知道为什么走霉运。原因找到了,一切都还有救。他火速开车回村,直奔村主任家。
大门紧闭,敲了半天,才有人来开门。是村主任老婆,头发蓬乱,双眼迷离。
“婶,我叔在不在?”他按捺心里的惊讶,把手里拎的两瓶五粮液递给她。
她接过,却说:“再好的酒有啥用,他也喝不了了。”
等进屋,看见卧在炕头的村主任,他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老村主任病了,病得很重,整个人已经脱相。
“没了庙宇,他死了怎么去那边呢?”他脑海里浮出这句话。
想问的已问不出,他只好说:“听说您身体不太利索,过来看看。”
老头挣扎着起身,靠住被垛,呼哧呼哧喘着说:“宏力啊,年轻一辈,就你有良心呀。老婆子,烧水泡茶。”
老太太先是翻药盒子,倒出一把药,递给村主任,然后冲了一杯茶给他。
聊了一会儿,他大概弄清楚了来龙去脉。村主任是在去年年初退下来的,也是在去年查出肺癌的。他退下来,是因为得病,而他的病却和庙宇有关。那一年,乡里推行退耕还林,有具体指标。但是,村里的田早就签了承包合同,没有谁家愿意为了一点补偿款把田退出来种树。村主任把一些沟沟坎坎的自留地凑起来,也还是不够,这时有人出主意,说庙宇那块地方,本来就是农田,现在为了它浪费这么多田,不值得,也没必要,不如拆了种树。村主任问他:“那以后送先人怎么办?”出主意的是个年轻人,叫马强,他说:“那还不简单,现在什么都能在网上办了,我们注册一个网上灵堂不就行了?又省钱又环保,而且还避免了山火风险。”
就这样,扒掉庙宇,种上了几十棵小树。但是这块地因为多少年没有种过庄稼,贫得很,那些树长得还没有秋天的禾苗高,远看上去,和周围的田连成了一片。
任务是完成了,但是老村主任很快查出了病,村里人都说,这是他拆掉庙宇的报应。
他听了老村主任的吐槽,心下一凉。他知道,自己当年的那个状元之名,就在老村主任这儿好使,在马强那儿啥也不是。马强他不熟,但这些年也有耳闻。以前,他只是个打工仔,在沿海一带的城市工厂拧螺丝。拧着拧着,觉得开了眼界,也攒下些钱,便回到镇上开了个五金门市,顺带修车。接着呢,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搞到了一个基层编制,借此回了村里,成了村委会的干部,几年下来,干成了副主任。他不干别的,只给村里招商,招了这么多年,没招来一笔正式投资,但他的能耐在于能搞到些小钱,把村委会的办公用房整修,还拉到赞助重建了村小学围墙。这一下,村委的人念他的好,村民呢,也把他当尊师重道的善人。要不是老主任在村里几十年,根深蒂固,他早就当上一村之长了。
从老村主任家出来,他直奔马强家。
马强很热情,双手握着他的手:“欢迎欢迎,大老板好几年不回村里看看了,还以为你把老家忘了。”
肖宏力顺着他的话寒暄了几句,然后直奔主题,问马强村子前面的庙宇。
“这也是响应乡里的号召,”马强说,“为了退耕还林,保护环境,也是为了倡导大家文明祭祀嘛。”
“那以后再有人走了,怎么送他们?”
“网上灵堂嘛,”马强说,“亏你还是大都市回来的人,现在都流行网上灵堂了,你想要啥效果都有,中国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鼠标一点,随心所愿。”
“那也不烧纸钱,不烧纸牛纸马了?”
“想献孝心啊,灵堂有公益捐款,与其把钱花在那些东西上,不如做好事,对不对?哈哈,这可是一举多得。”
半天,他嘟囔出一句:“也没有两间人了,以后再也没办法跟祖宗说话了,祖宗也保佑不了孝子贤孙了。”
马强笑了,说:“就你还信这个,村里人早就不信了。现在人没了,先拉到镇上烧成灰,再拉回山上埋进土。有的人埋都不埋,骨灰盒摆在家里的仓房,啥时候想给先人烧炷香就去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敬如在嘛。”
他感觉马强家的房顶特别低,天也特别低,整个苍穹似乎都在往下压。
前些年,他的确每年都回来,但只是走一遍流程,顶多看看老主任,很少在村里待。他已经完全不了解现在的村子是什么样了。不过,他大概知道,年轻人都进城打工,村子里多是老人和孩子,都是手里捧着一部手机,公放开很大声,看直播或者刷视频。
马强说:“老肖啊,咱们村穷,但是经过这些年的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山杏和中草药都长起来了,村里正考虑整一个加工基地,这样呢,能创收,也能留住年轻人。只是村办企业难啊,资金上还有点缺口,你可是大老板,能不能帮咱们村融点资或者拉点投资啊?当然了,如果你能亲自投资那就更好了。放心,只要你投钱,其他条件你随便提。”
肖宏力心里冷笑,想,我但凡有钱,也不至于这么着急跑回来。
他知道自己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马强,只得虚与委蛇,说:“钱总能找到的,不过,我这次回来,主要还是祭祖。可庙宇都没了,我这祖还咋祭?你知道,这可是我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我给祖宗烧多少钱,祖宗就让我赚多少钱。”
马强沉吟了一下,说:“我要是再把庙盖起来,你能投资?”
肖宏力说:“当然,不过,庙得建在原址上。”
马强大手一挥:“只要钱到位,你别说整个小庙,你就是要整个宫殿,我都给你建起来。”
他心里一动,从包里掏出一沓现金来,说:“建庙的钱我出。”
马强马上掏出手机:“我现在就安排,盖个小庙嘛,又不是盖大楼。一万块砖都用不了。”
三
新庙宇一周就建好了。
这庙不同以往,高度将近两米,三间,个子小的人几乎可以钻进去。红砖外墙又贴了瓷砖,屋顶有琉璃,也不是琉璃,是仿琉璃的玻璃制品,但在阳光下一样明晃晃。新庙宇整个看上去,就是很多景区里新修古式建筑的缩小版。
刚种下去没多久又被挖出来的几棵树,裸着根躺在一边,枝叶已干枯。肖宏力看着这崭新的庙,心里想,此处还能通向那个世界吗?愣怔间,马强已经指挥着几个人在庙宇前架起几个支架,上面摆着手机。他忽然明白,他们在搞直播。果然,一男一女,身着以前春节扭秧歌时才穿的红红绿绿的衣服,各在一个镜头前,开始大哥、大姐、家人们地喊起来。他听见了他们嘴里迸出的话:“今日,村里曾经的高考状元,北京的金融大鳄,富贵不忘家乡,回乡祭祖,老铁们,礼物走一波啊。”
他们自然不会知道,他今天就接到银行和信贷公司三个催款电话,到期还不上,他的一切都将被查封、拍卖。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次祭祖上。他幻想着,祖先保佑,期货几个板块能够解禁,股市能够飘红,让他东山再起。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时间不多了。多年来,他凭借自己的一手绝活,在各银行之间进行连续拆借,时间差打到分钟级别,从而赚到几千万的差价。但是这次,因为其中一个行长突然被带走,整个链条瞬间溃散。他也被带去调查问话,幸好他跟这个行长本身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一切手续都合规合法 ——时间点卡得再巧,毕竟不违法。
没有锣鼓,有的是直播音箱放的一首说唱歌曲,他只听清一句:临时抱佛脚,我只是临时抱佛脚……他似乎在短视频刷到过,心里想,这一句倒还挺应景。
站在庙宇前,他犹豫着要不要跪下来。这庙比它的前身高大不少,跪下后,再也看不见对面的田野和山梁,天空也被割去了一半。马强找人给他在镇上买了一大包冥币。他掏出一只打火机,点燃冥币,纸张燃烧起来,那种特殊的味道一瞬间灌满鼻腔。烟雾缭绕中,他终于找到一些熟悉感,只是耳朵里充满直播者的声音和另一首一个字也听不清的网络说唱。
他想张嘴,像以前那样说话,却什么也说不出。烟雾带着些许纸灰飘进嗓子,惹得他一阵咳嗽。他趁势多咳嗽了一分钟,心里盘算着怎么收场。现在看来,他必须得把这个金融大鳄继续装下去,只有装下去,祭祀程序才能完成;只有完成祭祀程序,祖宗们才能把那边的法力发向人间,自己也才有机会绝地逢生。
到这儿,想到这么多年他曾无数次逢凶化吉、大杀四方,信心又回来了。
他起身,快走几步,紧紧握着马强的手:“马主任,你放心,我一定全力支持家乡建设。我马上让人送钱来。”
不远处,几棵没有被挖掉的小树,似被这噪声和浓烟惊得呆住,一棵棵缩头缩脑。粗枝上,站着三四团黑色,风吹开烟雾再看,是乌鸦。他以为那些乌鸦会嘎嘎鸣叫,但是没有,它们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喧嚣的音乐声和人声、浓密的烟雾,竟然都没有让它们飞走。有几个瞬间,他怀疑它们是些假乌鸦,塑胶的人造品。但是,他又看见它们的指爪轻轻挪动,在摇荡的树枝上保持着平衡。
“也许,这些乌鸦就是沟通阴阳两间的使者,它们正凝神收集我所发布的信息,好准确无误地带给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和其他先人们。”他找到了最好的解释。
有人在推他,他定睛时,发现自己站在了手机屏幕前。
屏幕里是一个美颜变形的中年人,唇红齿白,花花绿绿的字幕在身上脸上滑过,还有一朵又一朵电子烟火绽放。他明白,这是直播间。他瞬间找准自己的角色,跟网友挥手问好,介绍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仿佛镜头里面才是保佑他的力量……
四
离开村子时太阳还没出来,他把车开到庙宇前。
他从未在清晨来过这里,晨雾温润,庄稼在微风中摇晃穗头。田野一片青绿,空气中氤氲着水雾,远远看去,庙宇像极了仙侠电视剧里的仙宫。他在田垄里走了走,谷穗带着微露,敲击他的大腿,像在按摩。有鸟雀啄食谷粒,平和的风中偶尔蹿出一阵急切之风,粮食互相摩擦,发出唰唰声。
风吹雾散,在这样的环境里,那庙宇因为极度清晰而看起来极不真实 ——他蓦然感觉到了它的突兀,不只是它建筑形制的新鲜、材料的新鲜,而是它整个看上去像是天外来物,如一面长满杏树的山坡上,突然间栽上了一棵梨树。
走到庙宇前,洞开的门吸引着他,走进去,走进去!
这一刻,他有种全新的冲动,那就是既然这里是通往冥界的入口,他可以由此进入新世界,离开现实,离开巨额的债务,离开喧嚣的人群,甚至离开庄稼地和庙宇,直接去到那些逝去的亲人的身边。
他走进去了。
眼前昏暗了两秒钟,接着庙宇里的情形渐渐清晰。香炉中,烧了一半的线香顶着灰烬的头颅,香灰的味道和复合建筑材料的味道混在一起,像熬了几个时辰的中药渣。
他咳嗽了一声,空旷的房间里回音震荡。
鸦鸣?
进来前,他特意瞥了一眼周围的树,没有乌鸦,什么鸟都没有。连刚才的麻雀也被稻草人身上挥舞的布条吓得飞走。
走过去,走过去!
供桌上龛位两旁的楹联,框出了一扇门的形状,门内虚虚晃晃。对联是他写的,还是那两句:从此去来世,到那莫回头。
他在龛位前跪下。前日他也曾跪在这里,但是心态已截然不同。
此刻,他感到庙宇无比广大深幽,仿佛整个宇宙。一抹香灰腾起,飞入他的眼睛。世界顿时模糊起来,揉搓半天,流了不少泪,才重新睁开。他知道眼珠肯定红了。
睁眼的瞬间,被突然而来的光芒晃了下。太阳从东方的山峦上升起,阳光投入庙宇之中,里面瞬间亮堂许多。
一只蚂蚱蹲在香炉前,刚才的香灰就是它跳跃时弹起的。
吱吱。它轻声叫着,并不着急跑走。他不由得想起多年前自己跪在这里的情形,恍惚中,他感到自己并未长大,更未经历后来的一切,仍然是那个孩子。它身上附着哪个祖先的灵魂?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还是他未曾谋面的谁?
他伸出手去,缓缓接近它。就在将要碰到的瞬间,蚂蚱后腿一蹬,跳到了旁边。他继续伸手,它继续跳。
如此几次,他们渐渐出了庙宇。
蚂蚱消失在田野中,又陡然间变大,分身为六。
不是蚂蚱,是人。他看见几个人影匆匆向这边跑来,手里挥舞着镰刀锄头。他认出了,领头的是马强。他们的声音先于他们的身体传来:“骗子,别让他跑了,砍死这个大骗子!”
昨日,在马强家里,他们喝了许多酒,都醉了。他按照承诺,把自己带来的一大笔钱 ——那印刷得跟真钱几乎一模一样的冥币 ——给了马强。喝酒之前,他收到北京的消息,已彻底破产,身背几千万的债务。
喊声越来越近。他愣怔了一下,连忙钻进车里,启动汽车。马强等人很快围了上来,锄头砸到车棚上,镰刀砍进车厢里。马强脸上狰狞,把一大捆纸钱抛向他。那些红红绿绿的冥币,在空中飞散,如彩蝶狂舞,一阵风来,成了五彩缤纷的旋风。
他发动汽车,猛踩油门,为了躲避那些人,车直接撞在了庙宇上。
庙宇轰然倒塌半面,龛位也砸坏大半,对联只剩下“从此去”和“莫回头”六个字。
他来不及细看,猛打方向盘,车轮碾过稻谷地,颠簸着驶上了乡村公路。
后视镜里,他再次瞥见坍塌的庙宇,心里竟生起一股畅快。
乡村的沙石路,他开到一百迈。石子被车轮卷起,溅到玻璃上,噼噼啪啪,鞭炮一般炸响。
吱吱!
他微微低头,心头大惊,一个急刹车,车滑行了十几米,撞在路边一棵树上,才停住。
仪表盘上,一只蚂蚱携带着风,冲着他的脸跳跃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