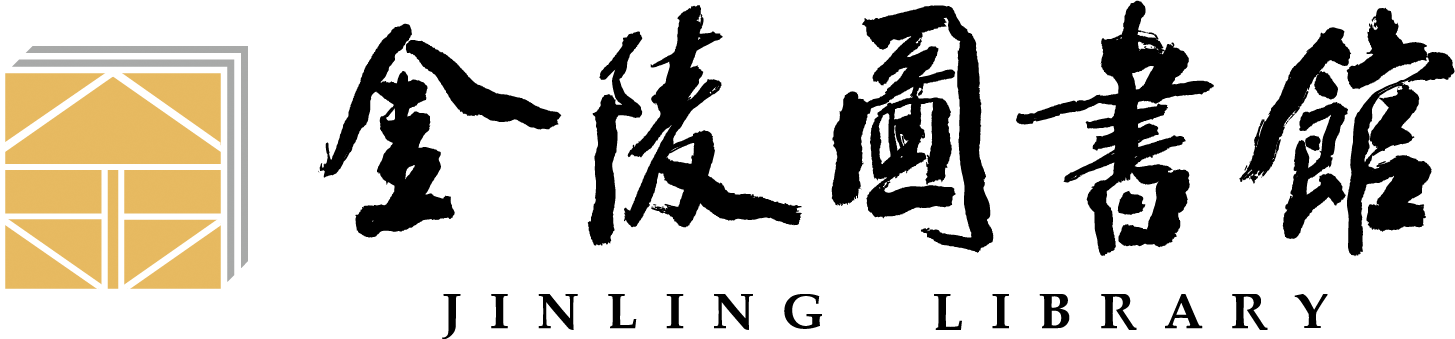![期刊架位号[8601] 期刊架位号[8601]](./W020240719361074212466.png) “对于流行的荒谬,要有抵抗的习惯。”
“对于流行的荒谬,要有抵抗的习惯。” 本刊记者/仇广宇
不少中国作家在作品中的“故乡”都有地理上的原型,能找到对应的地理位置。顺着这个思路,2023年年底,央视《文学的故乡》纪录片剧组来到山东寻访张炜的家乡。但这次,拍摄者却遭遇了难题。因为张炜出生的那片莱州湾畔的林野被大面积砍伐,林子中的独屋早已拆除,他在少年时就外出读书、游荡,很难说哪个小村庄是他具体的家乡,他的乡邻是谁。但这并不影响读者们通过他的小说追寻他的精神故乡。
三十多年前,张炜凭借《古船》《九月寓言》两部力作步入中国一流作家的行列,他的作品也成为文学评论界观察、研究的热门。但很多研究与观察似乎总是发生某种错位。比如多年来,外界一向冠以他“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中出现过这样的说教气息。
但张炜还是心平气和地接纳了这一切错位的解读,他也知道自己作品的阅读难度。他自嘲说,能连续读完他几本小说的读者,可算是“受累了”。不过,一旦习惯了张炜的叙述,读者就会惊讶于他书中宏大的历史视角,细腻的笔触和广阔的学识,也会顺利浸入他营造的那个世界里。这样的世界,是张炜多年来用钢笔和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搭建出来的,他发表的作品已经超过两千万字,每一个字都经过了他的手写。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不久前,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依旧是他手写完成的作品。
如此坚持古典写作方式的张炜,并不是一个和现代社会脱节的人。他常常看新闻,熟悉出版界的新动向,了解直播带货是怎么回事,甚至知道某些书在年轻人中走红起来的事,正想抽时间读一读这些书。虽然他不喜欢社交软件,但也会用微信沟通工作、记录灵感,当然也会用软件打车出行。
他只是选择和当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选择不与那些浮躁浅薄的人、事、物为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选择。三十多年前,在学界那场早已被人遗忘了的“人文精神论战”中,他在一篇名为《抵抗的习惯》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到:“对于流行的荒谬,要有抵抗的习惯。”这句话,至今依然可以作为张炜独特写作方式的注解。
想和年轻人对话
最近几年,张炜想和年轻人对话的愿望强烈起来。新书《去老万玉家》的封底上写着,这是一本“写给新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年轻人熟悉的当代,而是让它发生在遥远的19世纪末的胶东半岛上。他将故事的主人公设计成一位俊美、聪慧的年轻人舒菀屏,书中,在广州同文馆读书的舒菀屏为了完成恩师的托付,前往传说中能力超群的女匪老万玉的兵营探访。他经历了各种磨难挫折,也经过了对“圣女贞德”一样的老万玉的崇拜和幻灭,才最终逃离魔窟,获得成长。
听起来,这是一个作者在脑海中虚构的清末传奇,也像是一部年轻人的成长小说。但在张炜看来,这个故事并不是传奇,它是基于史实的严谨书写。书中,他所描写的地理环境、自然风物和大量的历史故事,都有其真实的来处。女主角老万玉的形象就来自三位草莽英雄传说的混合。小时候,他家附近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树林里面有一位面色黧黑,外形恐怖的年长女匪,让旁人不敢接近。后来,报纸上出现的一则美貌女匪的历史新闻也让他印象深刻。他把这两位女子的形象,和民国时期山东“胶东王”的故事混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书中的老万玉。
这样一个故事,背后背负的,是胶东半岛那一段没有太多人知晓的历史。19世纪末,胶东半岛曾有几股势力涌动:清廷的官军、地方的土匪、南来的革命军,还有不少前来传教、办医院的外国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复杂中也酝酿着全新的社会变革。张炜觉得,说起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如今的人们只知道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曾是先进思想的传播地,却很少有人知道,那时胶东半岛也曾引领风气之先。他希望,年轻人还是能以小说和故事的方式,去“接近真实”,去了解这些切实发生过的半岛传奇。
只是对年轻人而言,这部小说似乎还是有点厚重,充满复杂的隐喻和指向。相比之下,张炜出版于2022年的小说《河湾》接受起来更容易,也更有当代性。小说以一个网络暴力事件为引子,串起了主人公身边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婚恋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其中也描写了都市人使用聊天软件时不安、躁动的心理,以及网络谣言对真实生活的影响。最终,面对烦恼,男主角和朋友们只能到一处颇具自然情怀的“河湾”,暂时休憩,但“河湾”的存在,也不能让那些烦恼真正消失。
写作《河湾》时,张炜难得地从厚重的历史中抽身出来,直面了当代年轻人的困惑。他也将很多身边人的真实经历放在了书中。其实,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各地的大学教书、讲学,经常接触学生,也常常和年轻人沟通。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他和年轻人对话是困难的。在他看来,很多人的思想已经慢慢变得平庸化、简单化,在这种基础上,对很多问题难以展开理性的讨论。他想,争论不如告别,不如还是诉诸文字。“这本书就是写给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看的,希望他们知道‘暴力’的可怕。”他说。
尽管在这些小说中灌注了不少严肃议题,张炜的态度还是清醒的。他很清楚,时过境迁,现在读者要面对的娱乐手段五花八门,文学也早已不再如他年轻时那样,具备强烈的感召力量。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读者,在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由空调房、电脑和手机组成的室内生活之外,还有无数更复杂的生活、知识与经验,值得所有人浸入其中。
胶东半岛的流浪少年
在胶东半岛,随意说起一个地名,张炜就能还给你一段极具画面感的小故事。他回忆,在他小时候,在山东的蓬莱、龙口、莱州一带,冬天在海上、海边活动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耳朵是完好的, 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所有人的耳朵都冻烂了,到了春天,天暖了以后,人们都会有一个挺长的恢复期,整个耳朵干痒发红,慢慢地‘脱壳’,几乎每个人每年都要这样,就跟蚕蛹要脱硬壳一样。”他饶有兴味地讲着,仿佛看到了童年时海边那片“林野”中,那些耳朵残缺的人走来走去的场景。
虽然出生地已经消失,但擅长写自然和土地的张炜,作品中一直透露出浓重的故土意识,他自认是一个相当恋家的人。这一切因果的形成,都和他异于常人的经历有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炜外祖父的朋友在山东龙口莱州湾旁边的一片林野搭建了房屋。他的外祖父早年是一名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后来不幸牺牲,外祖母为了躲避追杀,就带着他们全家迁到了那间靠海很近的林中小屋,成了“独门独户”的一家人。
这样的环境,给了张炜一个孤独、奇异的童年生活。1956年,他诞生在这片离海很近的林野里,家里只有父母、外祖母,附近没有邻居,只有无声的大自然。在林间小屋的那些年,张炜的父亲在外地为水利工程工作,母亲也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回家,他大部分时间都和外祖母在一起。当时,只有三种人会来这个荒蛮之地的小屋里做客:采药人、猎人和打鱼者,这些人常有新鲜的故事,有时候还会留下猎物。张炜最初的社会交往就来自这些大人。此外,能够引起他兴趣的,就是家人留下的那些藏书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想象力也飞速滋长起来。
但一个孩子毕竟还是需要同龄伙伴的陪伴。于是,幼小的张炜常常长途跋涉穿过林场,到附近一个叫“西岚子”的、由流浪者集合成的小村庄里,去找小伙伴玩耍,他几乎去过那里的每一户人家,在很多人家里“蹭过饭”,喝过水。数年后,“西岚子”发现了煤矿、油田,变成了矿区,天南海北的人都在这里会聚,居民也换了一拨又一拨。通过这个村庄,孤单的张炜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特殊的家族史,迥异于常人的生活环境,敏感的天性,都注定了年幼的张炜迟早会被文学女神眷顾。事实上,他的人生剧本也确实是这么写的。读小学和初中时,校长是一位文学青年,他在学校里办了一本名为《山花》的杂志,是这位校长本人用手刻蜡版制作、印刷的。张炜给这本杂志写了很多文章,这种练习成为他未来文学生涯的启蒙,而杂志的油墨香气,一字一字的钢板刻印过程,变成了深深的记忆,或许也成了他至今还用纸笔写作的理由。
中学毕业后,张炜去了南部山区的叔叔家生活,不久又开始了在半岛上的游荡,这成了他救赎自己的方式。在乡野里,他在各处寻访像他一样,苦于作品无人问津的文学青年,向他们“拜师”,和他们成为至交好友。胶东半岛的大片土地上遍布了他的足迹,他也因此拥有了友谊和阅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累积了数百万字的习作,一直带在行囊中。漂泊的日子也有结束的一天。1978年,张炜考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两年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档案馆工作,在这几年里,他终于有了一张安静的书桌,也有了大量可阅读的历史资料。
很快,这个厚积薄发的山东青年开始让文坛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张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芦青河”的作品,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引发评论界热议。到了1986年,他的长篇小说《古船》在《当代》杂志首发,讲述在虚构的胶东洼狸镇中,三个家庭跨越四十年的兴衰历史,厚重的笔触和动人的故事在全国读者中引起反响,成为当年的一大文学现象。1992年,他又在《收获》发表带有魔幻色彩的代表作《九月寓言》,以一个无名小村中发生的光怪陆离的故事,再度震动文坛。
明眼人都看得出,《九月寓言》中的小村,《古船》中的洼狸镇,都是“西岚子村”的缩影。当年,他在村民身上获得的亲情和友谊,都已化为奇诡的文字和故事,流传至今。林中小屋里那个爱听故事的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位历史的“说书人”。而独特的经历,孤单的童年,也让他笔下的故事变得富有特色:它们似乎与沉重的现实和历史有关,又似乎略带魔幻,无法完全对应,就这样在细腻的讲述中,和现实保持着一份不远不近的疏离。
不停歇的“五十年代生人”
如今,张炜还在一笔一画地写着,但他感觉长篇小说的写作该停下来了。这样的长篇写作,对作家而言是体力、心力上的巨大考验。而写作新书的过程,最让他为难的不是那些繁复的史料,也不是繁重的劳动,而是对小说语言的把握。因为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清末,离现代有一定距离,他不能使用太过现代的语言表述,但因为小说内容也不是单纯的武侠或者传奇故事,又不能写得太像明清小说、白话小说。他还是在纸上写作,也必须字斟句酌才能下笔,否则不好修改。这些自我要求如同走钢索一般,让他吃尽了苦头。
张炜说过,自己的写作像是马拉松,这话放在他身上完全没有炫耀的意思,它完全就是事实描述,有时候,也只有这样马拉松式的写作才能完整地表达他对一代人、一段历史的看法。2010年,张炜推出了“小说史上最长的纯文学小说”《你在高原》,全篇一共四百五十万字,分为10部39卷,写作时间长达22年。在这10部书中,通过书的主人公、地质工作者宁伽的视角和经历,他为和他一样的“50年代生人们”写下了一部心灵史。他曾经借书中的一个角色之口,自述这群“50后”复杂的灵魂:“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统统都搅在了一块,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2011年,这部作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这种英雄主义,和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感,一直是张炜这代人的性格底色。他们似乎总要为历史和同辈人多留下一些什么,才能够放过自己。实际上,在多年前他创作《古船》时就隐约有这样的自觉了。当时他在长篇小说领域遇到瓶颈,却又一心想取得突破,凭着年轻人的勇气和心力,他最终只写了一稿,一鼓作气地完成了那本惊世骇俗的作品。如今想来,像《古船》《九月寓言》这样已经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他自己都很难超越了。
如今,有了23部长篇小说和大量随笔、诗歌,有超过两千万字的作品传世,获得了大奖的肯定,张炜似乎终于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现在,他每天下午都会到家附近的公园爬爬小山。回家后,他喜欢和自家的猫狗共享“天伦之乐”,家中那只胖乎乎的布偶猫憨态可掬,有一对引人注目的大眼睛,是女儿送给他的。每当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他就会忍不住变得更加感性。张炜爱美是出了名的,他的作品主角中很多都是英俊貌美的男女,可是在动物这里,他的审美标准完全妥协了。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长得难看的猫、狗,每一只都有它的可爱之处。
生活的愉悦,真的会让他就此停笔吗?或许没人能够知道。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在张炜心中,写作的标准和要求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一切都电子化了的世界,他还是坚持手写文字,手动修改,在多年之前物资匮乏的时代,得到稿纸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奢侈,他因此才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他说,电脑打出来的文字和手写的文字,不可能是同一种“味儿”。那早年形成的、用文字抵抗荒谬的习惯,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不会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26期 期刊架位号 [8601])